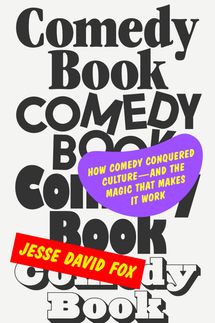九月,紐約客發表了一個故事克萊爾馬龍 (Clare Malone) 詳細介紹了喜劇演員和當時傳聞每日秀主持人候選人在哈桑·明哈吉的特別節目中,他似乎歪曲了事實,將自己集中在種族歧視的故事中或誇大了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在他的 2017 年 Netflix 特別節目中歸來之王例如,明哈吉談到一位白人約會對像在舞會當晚甩了他,因為她的父母不希望他們一起合照。當馬龍的報導對確切的時間表以及這一決定是否出於種族動機提出質疑時,明哈吉向她辯護說,這樣的決定是為了他的喜劇的「情感真相」。至少在社群媒體上,共識似乎是明哈吉錯了。然後在 10 月 26 日,明哈吉做出了回應非常哈桑·明哈吉風格的視頻事實查核紐約客在事實查核中,他辯稱記者操縱了引述並選擇不包含關鍵資訊。紐約客發表聲明支持他們的報道,但明哈吉的辯護足以讓公眾輿論分裂,認為哪一方更值得信賴。
這個故事說明了粉絲和各類旁觀者對喜劇演員可信度的看法是多麼投入。這部分歸功於 21 世紀的崛起每日秀政治喜劇節目提供了對新聞的看法,而主持人卻對被稱為「記者」表示不安。一個分水嶺發生在2004年,當時喬恩·斯圖爾特 (Jon Stewart) 出現在 CNN 節目中交叉火力並與真正的政治專家塔克·卡爾森和保羅·貝加拉對峙,許多觀眾在離開時感覺斯圖爾特是唯一一個有新聞誠信的人。同年,一個民調據透露,五分之一的 18 至 29 歲青少年是透過喜劇節目獲取選舉消息的,例如每日秀和週六夜現場。
到了 2016 年,隨著史都華停播、川普競選總統以及內容產業蓬勃發展,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可以信賴喜劇演員作為新聞或政治評論的來源。我們觀看了斯圖爾特追隨者(包括斯蒂芬·科爾伯特、約翰·奧利弗和薩曼莎·比)、福克斯新聞上的“有趣”專家的節目(格雷格·古特菲爾德和 Jesse Watters),以及來自 Dirtbag Left 的播客(矮子陷阱屋)到自由主義者式的喬·羅根擴展宇宙(提姆狄龍秀和臭鼬軍團)。明哈吉本人也有 Netflix 節目,愛國者法案,從 2018 年到 2020 年,強調了馬龍的論點紐約客文章稱,像他這樣的喜劇演員“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古怪的公共知識分子,並且在向公眾通報情況時,他們承擔了道德仲裁者的某種地位。”然而,這種看法讓明哈吉和他的同儕陷入了對立的現實之中:作為主持人,他是一位權威,應該向權力說出真相並遵守新聞標準;而作為一名喜劇演員,他是一位試圖從他的內心激發情感的藝術家。
過去 75 年來,喜劇演員與真相的關係不斷發展。雖然過去的漫畫滿足於講述老套的笑話或重複熟悉的比喻(妻子不好;婆婆不好;食物不好——而且分量這麼小!),大多數當代漫畫都同意他們的作品應該有一些核心內容個人的真實情況。他們只是對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有不同的看法。這種緊張氣氛是我在播客中採訪包括 Minhaj 在內的 200 多名喜劇演員時親眼所見的好一個過去七年。每個表演者都採取不同的方法來延伸、重新格式化和強化他們作品中的真實性。有些人力求 100% 準確,甚至與參與其材料的其他各方進行事實查核。其他人試圖表達他們的真相僅基於他們如何記住特定情況。有些人發明了故事和情境,但希望創造出一些東西感覺普遍忠於他們的觀眾。
大多數情況下,單口會從事實開始,然後根據觀眾的反應修改細節。當我們在 2020 年交談時,Bert Kreischer 告訴我他在製作他著名的作品時的突破「機器」的故事:意識到他太執著於能夠證明故事真實性的訊息。 「我想分享無法偽造的東西,但這是一個錯誤,」他說。 “我認為沒有人真正關心這是否屬實。”
以下摘錄自我的書喜劇書:喜劇如何征服文化——以及讓它發揮作用的魔力,我討論了單口喜劇演員如何在他們的表演中考慮真理的歷史,並介紹了一些表演者對這一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章是很早之前寫的紐約客故事發表了。您對明哈吉所做或未做的事情的感受很可能取決於許多個人因素,本文摘錄並不意味著阻止您做出評估。相反,本章提供了理解故事以及類似事件如何發生的背景。的希望喜劇書不改變什麼人們會想到喜劇演員和他們的喜劇,但是如何。我沒有使用「情感真相」這個詞,但我已經非常接近了。
快速總結「喜劇中的真相」概念的歷史。在1950 年代和1960 年代,「病態喜劇演員」——雪萊·伯曼(Shelley Bermans)、倫尼·布魯斯(Lenny Bruce)——受到戰後存在主義的偉大內向精神的啟發,成為真實性的典範。 “許多美國人試圖尋找‘真實的自我’,”邁克爾·J·阿倫 (Michael J. Arlen) 在這 紐約客關於這個運動。 「新的藝人除了在身份搜尋上大做文章外,還試圖透過揭露——或者無論如何,承認——他們的『真實自我』來贏得觀眾的善意和尊重。」十年過去了,萊尼·布魯斯生下了喬治卡林和理查德·普賴爾兩者都有相似的傳說,即避開主流觀眾和簡潔的演示,以換取更蓬鬆和“真實”的東西。 70 年代末,普賴爾模仿了各種形式的說真話如何相互交織以贏得觀眾的信任,將完美的行為印象與精確的觀察性喜劇相結合,並以開放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缺點和失敗,探索自己的內心。然後,為了回應 20 世紀 80 年代單口喜劇俱樂部的公司化,90 年代的漫畫透過(跟我一起說)「沒有賣完」來展現其真實性。例如,這導致比爾·希克斯(Bill Hicks)反對廣告,讓自己變得特立獨行,在採訪中說:「我將繼續做我自己。正如鮑伯迪倫所說,擺脫法律束縛的唯一方法就是完全誠實。所以我將繼續無法無天。以及 20 世紀 90 年代洛杉磯等節目中的另類喜劇演員歌舞表演每個人都被要求帶來全新的材料並討論他們以前沒有談論過的事情,對 80 年代僵化的觀察性笑話和緊張的、深夜準備的五分鐘集的反應是盡量不表演,信奉“少一點笑話;少一點笑話」的口號。更多你。
現在,許多這些理想被認為達到了頂峰——
路易斯·CK 在喜劇走向更加嚴肅的故事中,CK 在近十年的時間裡一直是喜劇的化身。這場慶祝活動的中心是「真相」。這洛杉磯書評 打電話給他“電視上最誠實的人。”紐約客寫於 2015 年,一篇關於新 CK 特別節目的文章”,“喜劇演員被視為誠實的民粹主義者:我們認為,笑聲不僅讓人感覺良好,而且還揭示了普遍真理。這種看法並不是憑空而來,而是透過真實的或看似真實的工作和行動培養出來的。
就像他之前的卡林和普賴爾一樣,CK 也有自己覺醒真相的傳奇。幾十年來,他一遍又一遍地創作同樣的荒誕主義材料,卻得到了同樣的結果——寫演出,但娛樂業對他表演自己的材料相對不感興趣——CK 在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取得了突破。指出養育馬拉鬆的那些趣事可以追溯到永遠——我兒子總是把事情搞得一團糟!我女兒去購物總是要錢!——但CK 坦率地表示,無論是稱他4 歲的孩子為“混蛋”,還是透露“我每天都會從我女兒的紅色小陰道裡刮幾次屎,這會讓人感到多麼噁心、無聊和煩人。做這個素材除了讓他更受歡迎之外,還讓他與觀眾有一種以前沒有經歷過的親近感。然後,他將繼續將這種坦率風格應用到他的所有材料中——無論是關於性、技術還是種族——同時慢慢地消除最初讓他達到這一目標的公開誠實。
他的誠實神話隨後得到了一些專業決定的支持。首先,他在舞台上的穿著就像一袋垃圾,穿著不合身的黑色T恤和黑色牛仔褲,呈現出白人男性的平庸。儘管決定不關心自己的外表既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嘗試,但這幫助他推銷了「我只是一個在這裡說話的普通人」的形象。而且,他還讓戴恩庫克接受批評偷了他的一個笑話,儘管現在回想起來,這兩個笑話都是對史蒂夫馬丁的老笑話的即興演繹。他每年都會推出新的特別節目,自行發行並允許觀眾支付他們想要的費用。但沒有什麼比他為 FX 節目所做的安排更能提高公眾對他作為真正藝術家的看法了,路易。被業界稱為“路易交易”,其中涉及 CK 接受更少的資金,以換取在節目中做一切事情的自由——主演、編劇、導演、剪輯——無需外部投入。路易影響了關於喜劇演員生活的半自傳式喜劇/正劇的擴散,而聲望情景喜劇更感興趣的是創造一種超現實的、抽象的、喜劇的基調,而不是硬笑話,但就公眾的看法而言,CK 所做的一切都是透過他自己散發出來——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形容——作者的氣質。在他的鼎盛時期,持有這兩種觀點的活躍和隨意的喜劇迷都認為他是當今最偉大的喜劇演員,他成為所有其他喜劇演員必須追求和評判的榜樣。
然後,在 2017 年,紐約時代發表了一個故事揭露了針對他的五項不當性行為指控。儘管過去曾稱此類行為的謠言“不真實”,但不久之後,CK應付這一切。我記得我覺得有東西破碎了。 「為什麼我們對他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我認為這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否認了兩年,」這位喜劇演員和奧斯卡提名波拉特下一部電影合著者耶娜·弗里德曼說,評估情況。 「如果你處於說真話的位置,然後你對別人進行煽動,我認為對很多人來說,這似乎是一種比未經女性同意在女性面前自慰更嚴重的輕率行為,或者讓很多女性的職業生涯因此而毀掉。人們都知道 CK 是個怪物。他在表演中經常談到自慰。但信任對於喜劇演員與觀眾的關係至關重要。如果沒有它,就不可能進行同樣的事情。單口喜劇很難將藝術與藝術家分開,因為藝術是藝術家。是的,CK的所作所為很糟糕,但也極具諷刺意味。 「最誠實的人」是騙子?
事實上,他從來都不是電視上最誠實的人。 2011 年,HBO 匯集了三位受人尊敬的單口喜劇演員和瑞奇熱維斯 (Ricky Gervais)說話搞笑,關於作為一名(男)喜劇演員的考驗和磨難的對話。其中有一個有趣的時刻,傑裡·宋飛(Jerry Seinfeld) 談論了他最喜歡的CK 笑話,但在此過程中將其重塑為聽起來更像傑裡·宋飛(Jerry Seinfeld) 的素材。熱維斯說宋飛把它變成了一個笑話,他認為 CK 甚至不會講笑話。他解釋說,「我只是[認為],這是一個為了我的快樂而崩潰的人。這是一個傾訴心聲的男人,告訴我他度過了多麼糟糕的一天」。 CK 將熱爾韋對笑話寫作過程的天真與他蹣跚學步的女兒們進行了比較,並說:“我試圖讓它看起來像是,'我只是把這個說出來',但我知道所有的動作。在這裡很難知道CK的真實想法,但我的解讀是,作為一名藝術家,他對自己的真理感興趣,或者他對真理根本不感興趣,但對他可以控制的真理的外表感興趣。除了CK之外,歷史上和現在的真相對於喜劇來說都是危險的,喜劇演員可以用“這很有趣,因為它是真的”來掩蓋基於有害刻板印象的笑話,並通過把自己塑造成說真話的人來傳播毫無根據的陰謀。對於路易斯·CK(Louis CK)來說,一直談論自慰並不難,因為這讓他看起來像是在自慰,但實際上並沒有處於危險之中。他不是脆弱的。為了讓喜劇有真實性,脆弱性是必要的。
加里·古爾曼 (Gary Gulman) 在 2019 年 5 月寫道:「我相信,脆弱對於創作令人難忘的喜劇至關重要。」這是他正在製作的系列劇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他每天都會在推特上發布一些笑話寫作建議。它繼續說道,「在最初的幾年裡,僅僅登上舞台是很脆弱的。作為一名專業人士,這意味著分享自己讓你不舒服的部分,但同樣重要的是,致力於這個笑話。我很快就了解到,當時古爾曼本人正在從他精心製作的異想天開的幻想和詳細的觀察喜劇的標準組合過渡到有關他與精神疾病鬥爭的材料,這幾乎結束了他的職業生涯。這些材料後來成為 HBO 廣受好評的特別節目大蕭條。我在觀看時意識到,如果一個喜劇演員願意放棄那些給予他們控制權的噱頭、技巧或動作,從而將自己交給觀眾,那麼就會出現一種非凡的脆弱性。
我想起了 Margaret Cho,在她 2001 年的特別節目中,我就是我想要的人冒著職業影響的風險,點出名字並揭露她主演的經歷的陰暗面全美女孩,第一部關於亞洲家庭的美國情境喜劇。該劇的失敗引起了很多關注,但曹試圖澄清事實,討論了她承受的減肥壓力,導致飲食失調,導致住院和吸毒。不知何故,她讓這一切變得有趣。在特別節目中的一個時刻,她談到在片場度過了愉快的時光後要回家,這時她接到了一位她信任的製片人的電話,製片人驚慌地告訴她,電視網“擔心節目的完整性”。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她告訴觀眾。 「我一直以為自己長得還不錯。我不知道我是[漸強為喊叫] 這張巨臉接管了美國! [微笑,然後變成假恐怖] 臉來了! 「這也是藝術家們汲取生活中感動他們的事物並創造出有價值的東西的經典故事,」她說,回顧特別節目 20 週年。 “它只是將一種古老的治療方式帶入這個喜劇、政治、性別、酷兒的時代。”
我想到蒂格·諾塔羅2012 年,她從胃腸道感染住院到分手,到母親突然去世,再到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四天后登上洛杉磯 Largo 的舞台,以《Hello》開始了她的演出。晚安.你好。我得了癌症。你好嗎?大家都過得好嗎?我得了癌症。你好嗎?諾塔羅的表演之所以如此令人難以置信,不僅因為這些是藝術創作的困難主題,而且是她真實的自我,帶著她實際上生病的身體,正在表演這些。在2020年Slate採訪,她提供了它的外觀和感覺的完美形象。 「我感覺就像一隻試圖站起來的小長頸鹿,」她說。 「我在舞台上從未如此脆弱或個人化。我沒有分享我的約會生活。即使我被診斷出患有癌症,我也打電話給我的經理說,“我不想讓鎮上的任何人知道我生病了。”我害怕我不能再工作了。
我想到瑪麗亞·班福德,她對單口喜劇的許多技巧都擁有純粹的技術掌握,但讓她與眾不同的是材料的難度水平。她被迫談論那些難以談論的事情。精神疾病的恥辱是如此普遍,以至於「精神疾病的恥辱」現在已成為每個人都熟悉的短語。但是,當班福德在 2000 年代初期製作有關心理健康的材料時,例如「我從未真正認為自己有憂鬱症,就像[變得諷刺地渴望] 被希望所麻痺」-提起這件事很可怕。顯然,與變態者和性虐待者不同的是,精神疾病導致人們失業、難以維持人際關係以及難以被視為社會的正式成員。
透過她們的工作,這三位女性都面對了流行的觀念,即在舞台上無所畏懼意味著什麼。無所畏懼經常被用來形容漫畫家不怕傷害別人,而它本應適用於那些害怕被傷害並堅持不懈的喜劇演員。這些喜劇演員的動機並不是想讓自己感覺更好——這就是醫生、藥物和健康生活習慣的目的。相反,他們有動力去提供幫助,即使是透過為聽眾提供他們自己痛苦的替代品,或者讓就困難的話題進行對話變得更容易。喜劇演員可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為觀眾提供最好地代表自己所需的詞彙和語言。如果與某事共存或處理某事的困難在於談論它所帶來的恥辱,那麼脫口秀就超越了談話,因為它能夠大聲說出脆弱的真相。如果它是可嘲笑的,那麼它是可以管理的。
班福德、喬和諾塔羅所代表的是真正的真實性,與流行的、建構的真實性形象形成鮮明對比。作家兼哲學家亞歷山大‧史特恩兩者之間的區別,正如人們通常認為的,真實性是一種虛假,是一種被“從我們內心深處的慾望中獲利的公司”所玷污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追求,而真正的真實性可以通過“抵制自我陶醉和幻想”和“承認”來實現我們對他人的依賴以及存在於我們生活各個角落的歷史偶然性。”這是一個點諾塔羅附和道當我在她取得突破近十年後與她交談時。她告訴我,當她遇到出席的人時,她感覺與他們有聯繫,就好像他們一起經歷了一些事情。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明白,」她告訴我,「我正在尋求幫助。我當然有朋友和家人,但我的母親和我的主要關係都消失了。當我失去生命中的那些人後,我會去一個黑暗的單口喜劇劇院尋求安慰,這並不算太瘋狂。正如信任喜劇演員會產生一種親密感一樣,當喜劇演員信任他們的觀眾時也會產生一種親密感。
真理是一個不可能達到的標準。重要的是“尋求真理”歌舞表演創辦人貝絲·拉皮德斯(Beth Lapides)向我解釋說,這不僅僅是「既成事實,例如『這是事實』。」搜尋不必無私地進行,但也不能自私地進行。它不能單獨完成。
2017 年初,約翰·厄爾利 (John Early) 和凱特·貝蘭特 (Kate Berlant) 在吉米法倫主演的《今夜秀》。就深夜節目而言,這是一個相當不尋常的節目。兩人一反傳統的安全形式,大膽地提出了關於單口喜劇是什麼樣子以及喜劇中的真相意味著什麼的新願景。
這個場景讓我想起了當我第一次採訪他:“那些表現自我的人,我們通過表現失敗的方式來了解他們的真實身份。”在攝影棚的遊客和美國中產階級觀眾面前做這樣的事情是有風險的,真假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立刻,這些觀眾甚至可能不會將任何表演視為喜劇,導致電視觀眾沉默四分鐘,令人難以忍受。然而,它仍然比其他選擇要好。 「單口喜劇的奇怪之處在於,你必須假裝是即興表演,」厄爾在節目中解釋道。你讓事情變得很奇怪與皮特·霍姆斯談論今夜秀放。 “這對我來說太尷尬了。”
幾個月後,當我去布魯克林的現場表演場地貝爾屋 (Bell House) 觀看厄爾利的表演時,我仍在想著這個場景。節目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他問觀眾:“你們知道直男比陰戶更喜歡什麼嗎?”厄爾利歪著頭,揚起眉毛,似乎很想知道。就連我這個出席的少數直男之一也被難住了。他的臉繃緊了,握緊了拳頭以強調這個答案。他壓低聲音,傳達出一種充滿激情的陽剛之氣,他告訴我們:“事實。”這是一個關於喜劇中真實表演觀念的笑話,這種觀念受到上一代喜劇演員的支持,但被CK 破壞了——年輕一代的喜劇演員在互聯網上和邊緣化的現實中長大,一直在質疑這種真實觀念。
到 2017 年的這個時候,人們已經開始說布魯克林的每個人聽起來都像厄爾利和伯蘭特。當紐約時代喜劇評論家賈森齊諾曼在推特上詢問是否每個人都在模仿伯蘭特、博伯納姆,後來繼續執導伯蘭特的《首場單口特別節目和一人舞台表演,回答說她是“一代人中最有影響力/被模仿的喜劇演員”和“千禧年的倫尼·布魯斯”。他解釋說,她「比其他人早五年」就在做「高度自我意識的解構主義表演自由主義的事情」。厄爾利和伯蘭特都去了紐約大學,厄爾利學習戲劇,伯蘭特創建了自己的專業,名為“喜劇文化人類學”,他們一起帶頭炸毀單口喜劇的一個特定方面:表演。
早期將他的喜劇視角歸功於他成長過程中目睹父母(兩位牧師)的困惑。 “這是我非常熟悉的人,我正在觀看他們的精彩表演,”他2017年告訴我的。 「而且,作為一個同性戀者,在你意識到之前,你會想,我被困在表演中。在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之前,你對真實意味著什麼的理解非常支離破碎。伯蘭特的父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美術家,其作品被惠特尼博物館收藏,母親在轉向佈景設計之前曾在實驗劇院工作,學分她對獲得表演研究碩士學位而不是藝術碩士學位的看法是,因為這是「一個以問題為導向、以批判理論為基礎的世界,你要對自己的表現和身份表現做出反應,並大量思考觀看與被觀看的政治。伯蘭特在喜劇領域所做的事情就像亞歷克斯·卡茨在藝術領域所做的那樣,例如1959年代有,一幅畫中描繪了他妻子穿著藍色連身裙的兩幅肖像,非常相似但不相同。在他的作品中,他反駁了任何肖像都可以捕捉到一個人的獨特性的想法,因為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情;伯蘭特正在反駁這樣一種觀點,即表演掩蓋了真實的自我。正如她向內森·菲爾德解釋另一位喜劇演員在他的作品中與真理的概念進行了鬥爭,「這種對真理的痴迷,以及對真實性或真誠的痴迷。這種關於自我的想法完全沒有虛構,或者不是捏造的……感覺越來越像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謬誤。朱迪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也在我與厄爾利的談話中出現,他們對厄爾利和伯蘭特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正如巴特勒在書中寫道性別議題,“當意識到原來的一切都是衍生出來的時候,笑聲就出現了。”
你沒有向觀眾展示「真實」的自我。這就是為什麼伯蘭特覺得閱讀熱爾韋的喜劇《CK》的喜劇很荒謬。 “‘看,多麼簡陋和原始。’這太有趣了,」伯蘭特向菲爾德解釋道。 「我們知道在表演中建構一個自我,就像走在街上一樣。因此,任何人都可以登上舞台,而不是成為演員或表演者,表演根本就不是一種建構,這太奇怪了。
正是這種喜劇哲學使伯蘭特和厄爾利走在了新喜劇先鋒的最前線。由於最初的另類喜劇運動是對 X 世代喜劇演員在喜劇俱樂部喜劇演員的表演中看到的某種虛假行為的反應,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新喜劇女王”正如我在 Vulture 的同事 E. Alex Jung 在 2018 年所說的那樣,他們反對上台表演的虛假行為,無論這意味著什麼,表現得都是真實的。這些喜劇演員並沒有假裝「我只是一個在這裡說話的普通人」。飾演喬·費爾斯通 (Jo Firestone),一位紐約另類喜劇演員兼作家今夜秀當厄爾利和伯蘭特表演時,曾經解釋過,“無論如何,單口喜劇都是撒謊”,無論你是在唱歌還是聲稱前幾天遇到了前任。她認為,如果喜劇演員要撒謊,那麼唱歌和跳舞“感覺更接近事實”,因為表演者並沒有假裝他們只是編造一些東西。 “如果我們都要表演並塑造這個角色,”她解釋道,“你不妨穿上一套衣服,穿上踢踏舞鞋。”儘管很少有人真正穿著踢踏舞鞋,但自 2015 年以來,我在參加的每場喜劇表演中都看到至少一位喜劇演員唱歌。一群新的喜劇迷被那些不支持自己表演的誠實性的喜劇演員所傷害,他們開始擁抱那些誠實地承認這只是一場表演的喜劇演員。至少對他們的觀眾來說,這是真的。
2011 年,伯納姆20 歲,但他發現自己在Showtime 節目中與喜劇真理祭壇上的四位傳奇人物——馬克·馬龍、雷·羅馬諾、賈德·阿帕圖和加里·山德林——決裂。保羅·普羅文扎的綠色房間。伯納姆穿著一件寬鬆的灰色 V 領 T 卹,頭髮蓬鬆,看起來就像一個伸著懶腰的八年級學生,四肢都插著牙籤。他一次沉默了幾分鐘。自始至終,馬龍和羅馬諾都以男孩般的方式對他不屑一顧,但在伯納姆詢問山德林如何調和單口喜劇之後,男高音發生了變化,伯納姆認為單口喜劇本質上是一種西方藝術形式,與東方哲學視角結合。尚德林當時正從喜劇中半退休,轉而專注於對佛教有更深入的了解,他解釋說,真正的答案需要太多時間,但簡而言之,就是「真實性」。對他來說,這個詞似乎意味著擺脫自我,擺脫對社會期望的恐懼。 “當我在舞台上看到你時,”山德林對伯納姆說,“我沒有看到任何虛假的時刻。”好奇的普羅文扎想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因為伯納姆的表演如此諷刺超然,以至於他沒有在舞台上展示自己。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伯納姆在接下來的十年中試圖找出如何表達他的答案,揭示他對喜劇真相難題的看法。
與他的朋友以及偶爾的合作者伯蘭特和厄爾利的道路不同,伯納姆在互聯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迫使他在誠實等同於公開揭露的時代,努力思考真理的含義以及誠實的樣子。與 2021 年裡面伯納姆接受了這個想法,並將其發展成一場精湛的冥想,思考如何在自我數位化斷裂的時刻表達自己,以及如何在被迫保持社交距離時與人建立聯繫。拍攝地點是他的賓館(一定很不錯),畫面中總是有設備,插頁式廣告顯示他正在設定鏡頭,這一切都給人一種壓倒性的布萊希特式的感覺。伯納姆在特別節目中一次又一次地對比他表演的現實主義和明顯上演的視覺證據,描繪了互聯網如何顛覆了真實與表演之間的區別。而且因為它不是單口喜劇,表演者和被表演者之間存在固有的障礙,伯納姆能夠對我們所有人都被迫參與的數位表演的本質提出質疑。
然後……最有趣的事情發生了。我上了 TikTok,在人們與流浪貓交朋友的視頻中,我看到了一個又一個青少年分析的視頻裡面,白人女性展示她們Instagram 上的照片,以證明伯納姆在“白人女性的Instagram”中釘住了她們,各個年齡段的人對口型唱著“All Eyes on Me”,就像歌詞一樣(“你感到緊張嗎?我很困惑:如此尖銳地反對線上表演的特別節目,怎麼會得到如此虔誠的線上表演呢?直到有一天,當我滾動時,我聽到了自己的聲音。或者至少我認為是我。聽起來就像是我,在鏡頭外,隱約同意伯納姆的觀點,因為他正在解釋引發恐慌的背後原因。使快樂。我又滾了更多。流浪貓。烹飪牛排的技巧。 “All Eyes on Me”口型同步。又是我。這次,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是我在和伯納姆說話2018年禿鷹節。我證實了這一點,因為那天晚些時候我又看到了自己的另一段影片。第二天還有另一個。有一次,喜劇演員摩西·斯托姆在 TikTok 上給我發了一條訊息:“如果你在這裡想到博·伯納姆,演算法就會向你發送 91 個你採訪他的影片。”
感覺很糟糕而且很奇怪。這讓我很不舒服。我覺得有必要回复這些視頻,說“這就是我!”作為將我自己與我的形象重新連結的一種方式。雖然我不喜歡這些,但這確實讓我理解了人們的反應裡面更好的。很多人都感覺非常糟糕,因為看到疫情的隔離如何反映了網路生活的自我隔離。我此刻所感受到的分離感正是許多從小只知道數字存在的人一生所感受到的。正如伯納姆在 TikTok 上向我解釋的那樣,“你的自我被原子化成一千個不同版本的你,它們互相觀察、互相盤點。”這讓我明白了山德林多年前在伯納姆所看到的一切。在拉里·桑德斯秀,Shandling 頗具影響力的 90 年代深夜秀諷刺劇,分隔前台和後台的幕布是對兩者之間鴻溝的一種寓言,阿帕圖會這樣說,“人們試圖表達的與他們實際感受的不同。”裡面探索當你不清楚自己在幕布的哪一邊時會發生什麼。
裡面不是現場表演。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有多次拍攝和攝影機設定。仍然,裡面是伯納姆的特別節目,它與人們的情感聯繫最緊密,儘管它是他最做作的,但正因為如此。它認為,消除技巧的嘗試實際上是技巧,但人們可以嘗試真正創造技巧。相比之下,圍繞發布裡面,喜劇演員開始流行在他們的特輯中加入紀錄片片段,就好像他們是提供數學證明的科學家一樣。 “看?”他們會說。 “這證明它是真的。”但人們在紀錄片中對像伯納姆這樣的人的行為也是一種表演,所以稱其為「真實」感覺是錯誤的。裡面感覺很真實,因為它的製造是誠實的。
在我看來,伯納姆正在追求令人欣喜若狂的真相,這是電影製片人維爾納·赫爾佐格提出的想法,他以在紀錄片中加入虛構元素而聞名,例如安排他的拍攝對像或讓他們表演腳本場景。赫爾佐格相信事實是膚淺的,並且拒絕電影的真實性,他追求的是內心的、更深層的事實是“神秘而難以捉摸,只能透過虛構、想像和程式化才能達到。”這就是為什麼米開朗基羅把一個大腦袋和一個戴著烤箱手套的大手拍在他的身上。大衛,知道人們會從下面觀看這座 17 英尺高的雕塑,並了解誇張是必要的,這樣才能使其顯得真實,甚至更加真實。
伯納姆的部分人明白,單口喜劇演員(也經常從下面看到)也會這樣做,因此如果以其他方式拍攝他們可能會讓人覺得不誠實。裡面這並不是對伯納姆疫情大流行的字面描述(他可能睡在自己真正的房子裡),而是一次真實的嘗試,試圖捕捉他想要傳達的訊息。人們不應該從字面上理解,讓特殊人士擔心他現在是一個自殺的隱士,而應該讓那些在大流行期間可能經歷過困難的人們擔心。與CK的「真相」的私利相反,伯納姆提供了一個可以幫助觀眾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真相」。伯納姆的目標,就像山德林一樣,從來都不是個人真相,而是事實──就這樣。
改編自喜劇書,作者:傑西大衛福克斯。由法勒、史特勞斯和吉魯出版。版權所有 © 2023 傑西大衛福克斯。版權所有
您透過我們的連結購買的東西可能會賺取沃克斯媒體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