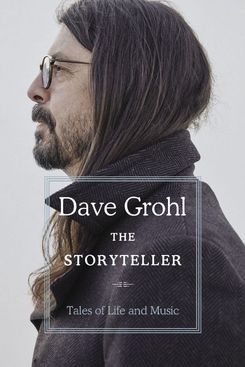我遇見戴夫·格羅爾九月中旬後的第二天噴火戰機幾乎沒有發生的演出。揮之不去的大霧使樂團的私人飛機在甘迺迪機場停機坪上滯留了近四個小時; Live Nation 要求成員錄製一段視頻,在擁有 17,000 多個座位的錫拉丘茲聖約瑟夫健康圓形劇場內播放,並宣布演出已被取消。就在格羅爾打電話之前,他從飛行員那裡得到了警報。噴火戰機在警察護送下衝進聖喬教堂,以勝利的“Times LikeThese”開場。對於這位搖滾樂手來說,天氣延誤並不是什麼難事,他在 1990 年離開了備受推崇的 DC 朋克樂隊 Scream 後才成為了舞台主唱。涅槃,他的快速崛起隨著他的去世而戛然而止科特·柯本四年後。噴火戰機 (Foo Fighters) 是一個以一批獨奏演示開始的項目,後來發展成為龐克和情緒搖滾老手的兄弟會,引入的進入搖滾名人堂這個週末,戴夫在 2014 年 Nirvana 就任後兩度獲獎。說故事的人:生活與音樂的故事,格羅爾正處於沉思狀態。
那是 1991 年的秋天。沒關係被釋放。它在最初幾週內就賣出了幾千份。到今年年底,它每週的銷售量已達到數十萬件。您什麼時候注意到事情發生了變化?
我們很高興沒有意識到很多事情,因為我們被困在一輛貨車裡,一輛 U-Haul 拖車停在一些小俱樂部,並將我們自己的裝備裝載到演出中。我記得“Smells Like Teen Spirit”視頻在 MTV 上首次亮相的那天晚上120 分鐘。庫爾特和我曾經共用一個房間。我們知道它會出現在節目中。那天晚上,我們意識到我們已經從一支帶著 U-Haul 的貨車裡的樂隊變成了電視上那輛帶著 U-Haul 的貨車裡的樂隊。但那時我們進展得很快。我認為直到幾個月後我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注意到的是演出現場的人數。我們預訂了華盛頓特區的 9:30 Club 等場所,該俱樂部可容納 200 人。你把車停到演出現場,會發現俱樂部裡有 200 多人,外面還有 200 多人想進去。
現在情況很不一樣了。人們確實對數字很敏感。
我不認為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開始演奏音樂時都會考慮到職業。你愛上了披頭四樂隊,你拿起一個舊樂器,它就變成了這個謎題或這個遊戲。你會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都被同樣的迷戀所困擾。你開始在地下室播放自己的爛歌。也許你在人們面前這樣做,你開始渴望與觀眾建立這種關係。其他的事情,如果有的話,也會晚得多。現在是一個不同的世界了。我確實認為,當我看著我的女兒們學習演奏音樂時,她們的起點與我相同。初心是真誠的,而且永遠不會消失。
1992 年,您發布了懷錶Tape,你的第一個個人項目,化名 Late!你什麼時候意識到科特·柯本知道你的副業項目?
當我第一次加入樂團時, 我為他們播放了一些我在弗吉尼亞州錄製的東西尖叫之旅。所以他們知道我自己錄製了一些東西,但它們只是這些小小的聲音實驗。我只是在抽大麻,沒有其他事可做。這又回到了那個著名的老笑話:鼓手被趕出樂團之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 “夥計們,我有一些我認為我們應該演奏的歌曲!”認識到庫爾特作為詞曲作者的才華,我不會試圖擠進去。我當時想,我知道我在這個樂團中的角色是什麼。我需要敲起鼓,像壓路機一樣將這些歌曲推向觀眾。
我有一盒錄音帶。我為庫爾特和貝斯手演奏它們克里斯特·諾沃塞利克有一天在麵包車裡。在某個時候,我回到了弗吉尼亞州,和我的朋友 Barrett Jones 在他的 8 軌唱片上錄製了更多狗屎。我的朋友珍妮·圖米有一個標籤。她聽到其中一首歌後說:「我正在做一個合輯。你想在那裡放首歌嗎?我做到了。然後我開始嘗試寫歌。以前,它們只是這些瘋狂的龐克搖滾實驗。我錄製了歌曲“Floaty”和“Alone + Easy Target”。我為他們感到驕傲。我記得為庫爾特演奏過“Alone + Easy Target”。他吻了我。我絕不認為,好的,這將出現在 Nirvana 的下一張唱片中。寇特承認我是一個可以寫歌的人,我感到受寵若驚,也很高興。
格羅爾,1993 年 12 月。照片:傑夫·克拉維茨/FilmMagic
當他聽到那些他邀請你為 Nirvana 創作的早期歌曲時,你是否希望他參與其中?
不。所以我們從來沒有使用過它。在 Nirvana 的最後一次會議中,我們錄製了一首名為“You Know You’re Right”的歌曲。我們坐在工作室裡等了科特幾天。在那段時間,我錄製了《Exhausted》,這首歌最終成為了《Foo Fighters》的第一張唱片。庫爾特也喜歡那個。但沒有。我不想混淆他的過程。
後沒關係, Nirvana 與製作人聯手史蒂夫·阿爾比尼為了在子宮裡。與之前的記錄相比,它更具對抗性和磨練性。來自標籤的壓力要求打磨粗糙的邊緣。對於一支從來不需要聽取外界關於其音樂的意見的樂團來說,這一定很尷尬。
身為鼓手,當時我不一定參與任何這些職業決策。它並不總是「一切為了一,一為了一切」。當我們製作的時候在子宮內,人們非常關注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這種壓力施加在庫爾特身上,我相信他要清楚地應對這一點並不容易。我在他媽的三天內就完成了鼓,然後我坐在旁邊看著剩下的事情發生。當我們帶著這些混音回來時,唱片公司的某人說:“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和在子宮內是…我不想說這是我最喜歡的 Nirvana 唱片,但它對我來說絕對是最強大的。
這是我最常回顧的一次。
這是一張複雜的唱片,但我很高興全世界都能聽到它。我喜歡現場演奏這些歌曲。我希望我仍然可以。我已經做過幾次了。我玩過「心形盒子」。
你不是時不時撕扯《無香學徒》嗎?
我是說,我已經老了,老兄。不。安妮克拉克或者貝克,或者和我女兒一起,我們演奏一首像《心形盒子》這樣的歌曲,我用這些鼓敲打的力度比 30 年前還要用力兩倍。我很想念它。
記者麥可·阿澤拉德寫道一塊最近,他在 Nirvana 周圍發生了一些故事,其中一個引人注目:他說在美國巡迴演出期間有一晚在子宮內當庫爾特在他的飯店房間裡大喊要解僱你時他告訴庫爾特,你在隔壁房間很可能聽到了他的聲音。我想知道你是否這樣做了。
我沒有,而且我對這個故事有不同的版本。我們正在前往洛杉磯的路上,開始為電影進行製作排練。在子宮內巡迴演出時,我坐在科特和克里斯特前面幾排。我能聽到庫爾特說,「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更基本的鼓手,就像丹彼得斯那樣,」他是他們幾乎僱用的人當我加入樂團時。我真的很沮喪,因為我以為一切都很好。我和克里斯特談過,我說:「這真的是你們想做的嗎?因為如果這就是你想要的,也許只要告訴我,我們就到此為止了。我最終和庫爾特談論了這件事,他說:「不。這不是我們想做的事。我只是覺得,就看你們自己真正想要什麼樣的鼓手了他們決定我應該留下來。
樂團距離解散或徹底重組還有多遠?
誠實地,在去年,你每天醒來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的處境不穩定有很多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樂團的突然成名給我們帶來了創傷。我不能為庫爾特說話,而且通常也不會,因為他不在場為自己說話。我們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處理它,但最終這是一件很難駕馭的事情。我們迴避了主流的商業吸引力,在我們他媽的陰影後面的世界裡感到非常快樂。然後我們就成為其中的一員他們。你他媽的怎麼處理這個?樂團內外一片混亂。為了寶貴的生命,你必須堅持下去,並希望旅程不會停止。
你是否曾經糾結過要對庫爾特保密什麼?
一點也不。我會選擇性地告訴大家。事情是這樣的:涅槃就是人。很難記住它什麼時候成為一個標誌或一件 T 卹。最後只有三個人寫歌,開著貨車到處巡迴。當涉及到非常私人的事情時,我選擇與最親近的人分享。如果我的女兒們問我有關 Nirvana 的問題,我會回答每一個問題。
當你成為自己樂團的主唱時,你是否開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科特?
我在《Nirvana》中學到了很多關於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的經驗教訓,我將這些經驗應用於成為 Foo Fighters 的歌手。出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有伯尼·桑德斯式的公式來發布每首歌曲。您不必演奏或創作這首歌,您仍然可以發布它。它消除了對話,這樣你就不會陷入任何內在衝突。搖滾樂的歷史一再充滿著同樣的古老故事。對我來說,最好的想法就是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並為所有事情制定這個公式。
你的職業生涯中沒有發生過任何重大醜聞。你是怎麼做到的?
我會回到庫爾特去世時。第二天早上,我醒來,意識到他不會回來了,我很幸運又度過了一天。我坐下來煮了一杯咖啡。今天我可以喝杯咖啡。但他不能。我鑽進車子去兜風。美好的一天。太陽出來了。我正在經歷這件事。他不能。就在那時我意識到,無論一天是好還是壞,我都想活著去經歷它。這將成為你的占卜棒。我只想到達明天。我他媽的只想再多一天。尤其是在——我不會說「在這樣的時期」。
我覺得這對你們經久不衰的歌曲至關重要:“Times LikeThese”,但我也在考慮“Everlong”和“My Hero”。那些流傳很遠的歌曲都是關於拾起它並繼續前進。
我無法寫一首關於未發生的事情或我沒有感受到的事情的歌曲。重新開始的概念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我一生中經歷過不只幾次。你走到了十字路口,你必須引導你的道路。當噴火戰機製作時顏色和形狀,我經歷了太多該死的事。我無處可住。我正在經歷離婚。帕特他媽的要離開樂團了。鼓手已經他媽退出了。我口袋裡他媽的沒錢。我睡在我朋友的後面房間。他的狗每天晚上都在我床上尿尿。我準備好抓拍了。我有這些日記;我將逐一列出這些問題。我會看著這個清單然後想,好吧,如果我同時想到所有這些事情,我就會精神崩潰。如果我一次專注於一個,也許我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也許我能撐過去。所以我盡量不被正在發生的一切淹沒。我一次只擊打一件事。
我相信這些年來你已經聽過無數次這樣的說法:第一張 Foo Fighters 專輯有點像喬治哈里森 (George Harrison)一切都會過去情況。世界上最大的樂團解散了,而你卻帶著一張偉大的專輯重新站起來。你常聽那張同名唱片嗎?
我不久前聽過。從聲音上來說,這是一張瘋狂的唱片。
這聽起來與 1995 年的情況並沒有太大不同。
部分與聲學環境有關,部分與緊迫性有關。這個工作室與我一生中去過的任何其他工作室都不一樣。它建在山坡上。它就像一個巨大的碉堡。直播室、跟蹤室都是石頭和大理石。大多數人會認為這樣的聲學環境過於惡劣。我們花了六天的時間,我寫了 14 首歌。而且只有一個人在玩這種狗屎。所以我可能會花兩個小時來聽一首歌。所以我會一次完成鼓音軌,然後我會跑去製作吉他音軌,也許加倍,在上面放貝斯,然後把它放在一邊。所以在大約 1 小時 15 分鐘內,我就完成了器樂曲目。我每天必須做四次。目的不是要錄唱片。他媽的就是為了把這些歌錄成24軌。
您曾在地下室和車庫、專業和個人工作室錄音。作為製造者聲音城,一部完整的紀錄片,講述了這個錄音室提供的美妙聲音,您似乎正在尋找完美的房間。
好吧,在我錄製過的所有房間中,Sound City 是您能找到的最接近的房間。洛杉磯工業園區舊倉庫的魔力。這是無法定義的。不明白為什麼房間聽起來是這樣的。確實如此。這就像他媽的工作室的百慕達三角。
在你的回憶錄中,你說你選擇了 Sound City 來錄製沒關係部分原因是它的優勢是離格芬唱片公司辦公室足夠近,可以確保你不會“再進行另一場偉大的搖滾騙局,就像性手槍樂隊那樣(我們曾經考慮過這一點) ”。請談談這一點。
我認為唱片公司希望我們靠近,這樣他們就可以監視我們。因為我們本來就沒什麼人。他們將交給我們這張大支票……其實並沒有那麼大。我不知道,是 35,000 美元。不管是什麼,他們都會把所有這些錢交給我們,並祈禱他們能創下紀錄。當所有這些唱片公司向我們求愛時,他們會飛往西雅圖或塔科馬,帶我們去貝尼哈納,出示信用卡,告訴我們他們將給我們一百萬美元,然後我們就回到這個破爛的小公寓,我們幾乎沒有錢吃。當一家唱片公司說:“我們今天會給你一百萬美元”,你會怎麼做?你說不。這就是毒蘋果。或者你拿著它,進行一場搖滾詐騙。我們非常熟悉性手槍的故事。我認為我們做了正確的事。我們跟隨音速青年的道路。我們找到了音速青年隊的經紀人。我們用他們所貼的標籤簽名。他們開闢了道路。他們讓我們這樣的樂團能夠安全地獲得唱片合約。
你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都在努力尋找穩定的樂團環境。尖叫聲爆發,隨後涅槃。我幾乎把《噴火戰機》視為你的來世。有沒有發生過很多動盪?
你已經到了無法分手的地步。十年不再玩,但不要告訴任何人你分手了。就像你的祖父母離婚一樣。你他媽的要這麼做是為了什麼?如果你看看這個樂團的基礎,我們四個人都來自過早結束的樂團。內特·孟德爾(Nate Mendel)和威廉·戈德史密斯(William Goldsmith)來自當時西雅圖最酷的樂隊 Sunny Day Real Estate 樂隊。他們的歌手傑里米·恩尼克 (Jeremy Enigk) 找到了上帝,並且樂隊關閉了。我正在考慮組建這個新樂隊,但我不認識任何人。我和內特有一個共同的朋友,他說:“他們要分手了,這個週末他們有一場演出。”我下去看看演出。我想,他們在一起玩得很好。我會給他們一盤錄音帶。也許我們會去塞車。我們做到了。我們的第一次練習是在威廉·戈德史密斯(William Goldsmith)他父母住的房子的地下室裡進行的。我們把它組合在一起,幾乎就像你在高中組樂團一樣。
派特和我,來自 Nirvana——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轉變,因為當 Nirvana 結束時,我認為沒有人想再次創作音樂。一想到科特不在場,坐在鼓凳上我就心碎。前兩天晚上我又夢見他了。我常常夢見他。在夢中,樂團重新聚在一起,我們再次這樣做。這是一次旅行。克里斯特、帕特和我對這些歌曲的看法與其他人不同。當我們演奏它們時,它會提醒我們生命中的那段時光是多麼遙遠,以及再次演奏的感覺是多麼自然。噴火戰機的整體概念是成為生命的延續。庫爾特過世後,樂團裡一個叫 7 Year Bitch 的人寄了一張卡片給我。它說:“我知道你現在不想演奏音樂,但你會的,這會救你的命。”他們是對的。我花了一段時間才到達那裡,但噴火戰機仍然救了我的命。
我在想我是聽著垃圾音樂長大的,以及它如何成為關於死亡的早期且揮之不去的教育。我們失去了科特·科本。我們失去了萊恩·斯特利克里斯康奈爾,來自 Hole 的 Kristen Pfaff,來自 7 Year 的 Stefanie。當場景發生時,你有沒有感覺到鬧鬼的感覺?
不,我的意思是,我來自華盛頓特區,從未接觸過海洛因。我還沒拿過。華盛頓特區並不是真正的海洛因小鎮。西雅圖是海洛因之都。這是東部的一個港口。這狗屎就這麼進來了,更不用說一年中五個月都是灰濛濛多雨的環境了。酗酒率如此之高,而且到處都有大量吸毒和海洛因。我剛到那裡時並不明白這一點,沒多久我就意識到這座城市是海洛因之都。所以,不。但我會告訴你,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多年來,當我們失去一個人時,我會看到他們的樂團成員,這讓我心碎。我去了克里斯康奈爾的紀念館,我站在那裡和《愛麗絲囚徒》中的一些人交談…
誰失去了兩名成員…
我會看著他們的樂團成員並想,哦,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夥計。
快轉到第二張 Foo Fighters 專輯的片段,顏色和形狀。當你重新錄製戈德史密斯的鼓時,他退出了樂團。
我們從 96 年秋天開始錄製唱片。我們在西雅圖郊區預訂了一個名為 Bear Creek 的工作室。我們有一位製片人,吉爾諾頓。他是英國人,因製作 Pixies 唱片而聞名。我們寫了一些歌曲,正在進行前期製作。我以前從未與吉爾合作過,但很快就發現他不會在工作室裡亂搞。他是一個工頭,一個拼命、拼命、做 50 次才把事情做好的製片人。我很喜歡它。但這很難。當我們進行前期準備時,每個人都爆發了。我記得排練後看到內特把他的貝斯丟進了他媽的垃圾桶。我看得出來,威廉不太習慣製片這麼辛苦。我一個接一個地進行聲樂拍攝。我就像,他媽的。我他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歌手。我可以看到它戴在威廉身上。
所以我們在聖誕節期間休息了一些時間。我回到華盛頓。我寫了兩首新歌:《Walking After You》和《Everlong》。我在大約一個小時內演示了它們。此時,我們已經到了最後期限,我們已經搬到洛杉磯來完成這張唱片。我帶著這兩個演示回來了。吉爾說,對於《Everlong》,“我認為我們應該重新錄製這首曲子,讓它變得很棒。”他說:“我認為你應該打鼓。”我就像,“操,夥計。”與此同時,威廉在西雅圖。我們這樣做了,吉爾說,“那另一首歌怎麼樣?”我想,「只是這首歌的快速部分。好的。我開始重做鼓。我就像,「操,夥計。我必須打電話給威廉並告訴他我們正在重做一些鼓。我應該早點打電話給他。當我打電話給他時,他真的很沮喪,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在某種程度上後悔這樣做了。我飛到西雅圖和他談談這件事。他說:“我要退出樂團。”我想,「不,不,不,不。留在樂隊裡。成為鼓手。播放這些歌曲,我們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他說不。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說的一件事:“實際上,我的朋友給了我一份挖溝渠的工作。”我說:「真的嗎?你知道嗎?你應該這樣做一段時間。我以前挖溝渠。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在弗吉尼亞州炎熱的夏天,我做過他媽的石工。去挖一些溝渠一段時間,然後你會想成為鼓手。是的,它有點崩潰了。我懇求祂留下來;他拒絕留下來。這是底線。
格羅爾和威廉‧戈德史密斯,1996 年。照片:Ron Galella Images/Ron Galella Collection via Getty
編按:紐約聯繫了戈德史密斯,戈德史密斯回應道:“帕特、內特和戴夫去了洛杉磯,我在西雅圖等待消息飛來完成這張唱片。”在沒有收到任何消息後,他聯繫了管理層並要求他們為他預訂航班。他說,就在那時,他接到戴夫的電話,戴夫要他先不要下來,並告訴他他們正在重做幾首歌的鼓。 「無論如何,我飛到了洛杉磯,」戈德史密斯說。當他到達洛杉磯時,他入住了樂隊其他成員所住的同一家酒店。 「那天晚上晚些時候,內特在大廳遇見了我,」戈德史密斯回憶道,「當我問他重新錄製幾首歌曲的情況時,內特的回答是,『他是這麼告訴你的嗎?他正在重新追蹤他們所有人.'
「我們連續三週每天追蹤唱片上的鼓長達 13 個小時,其中一次對一首歌曲進行了 96 次錄音。因此,因為戴夫想在兩首歌中打鼓,我就放棄一切的想法是荒謬的,」戈德史密斯繼續說道。正是“發現我所做的所有工作都被忽視了,才導致我決定離開。”他說格羅爾確實要求他留在樂隊,“在我為唱片所做的所有努力都被忽視之後,我無法證明這一點是合理的。”他補充道,“然後我開了個玩笑,說‘世界也需要挖溝者’,這是一個球童小屋參考資料,但我猜他沒有明白。
陽光天地產幾年前,我們在你們的工作室重聚並製作了第五張專輯。這張專輯從未實現。戈德史密斯出來說,你對這張專輯的失敗負有一些責任。他收回了聲明,但仍然有點牽連到你,因為工作室的老闆,在會議上不成功。
你應該問他最好的老朋友內特·孟德爾(Nate Mendel)這件事,因為他在那些該死的會議期間就在那裡,他確切地知道發生了什麼。
是的,內特說這些言論沒有事實根據。我想知道你對這一切有何感受。你覺得這麼多年過去了他還是不高興嗎?
我的意思是,他們試圖錄製唱片,但沒成功。你聽過那張唱片嗎?
我們聽到了一兩首歌。 《立頓女巫》還不錯。
是的。我的意思是,說實話,我不會給這種事任何頻寬。當它如此缺乏任何現實時,我什至不打卡。
你的回憶錄首先詳細描述了身為主唱對你的身體造成的一些傷害。你有沒有考慮過放慢腳步?還是今年就是這樣?原本的計劃是進行這次快速、緊湊的巡演,但最終你還是在競技場上進行了約會,中間有很多喘息的空間。你是放鬆心情還是只是隨機應變地度過這一年?
當我摔斷了我的腿,我記得我以為這是來自宇宙的訊息,告訴我要冷靜下來。你並不是無敵的。你很脆弱。你需要放慢速度。我考慮了一下,然後又去巡迴了 65 場演出他媽的椅子上。我真的很享受我所做的事情,而且我在創作上焦躁不安。
我2018年在麥迪遜花園廣場見到你。有一種精確性,我認為這是噴火戰機的標誌。從這方面來說,它無疑是一支鼓手樂團。不過,你確保沒有任何事情是照本宣科的。這是一種自由。
至於將樂團聚集在一起並確保歌曲緊湊而有力,我們會盡力做到最好。但在音樂上我們有一句話:如果它變得更好,它就會變得更糟。我們排練到一個要點。我不喜歡在歌曲中間排練冗長的即興演奏部分。他媽的。當它發生時它就會發生。我不想編排那個。讓我參加下一場演出的原因是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尤其是在他媽的26年後。我的天啊。沒辦法啊大型演出的親密感部分在於不僅讓觀眾參與其中,而且讓他們清楚地看到舞台上的人。隨之而來的是一種鬆散的氛圍,我和帕特在舞台上互相做愛,或者我和鼓手泰勒霍金斯在一首歌中徘徊在危險的即興領域,你會說,“去合唱吧,混蛋。”
談論拖釣韋斯特伯勒浸信會抗議者十年來你不斷地炫耀。
這太容易了。他們開始糾察我們的原因是我們曾經製作過一個旅遊廣告,其中我們所有人一起洗澡。我想這他媽的讓他們怒火中燒,他們決定每次我們在堪薩斯城的時候都來糾察噴火戰機樂團的演出。如果他們不是那麼殘酷地冒犯我們,我們不會在意,但他們所代表的東西是可怕的。當他們出現在你家門口時,你必須把他們推回去,當然,我們會以我們一貫的方式做,要么用力滾他們,要么播放 Bee Gees 的歌曲,要么停在平闆卡車上玩對於他們來說。但我必須誠實。當某人看著你的眼睛並尖叫著「戴夫·格羅爾,你會在他媽的地獄裡被燒死」時,看到他們眼中充滿仇恨,而他們他媽的就是這個意思。就像,哇。我只是站在那裡演奏 Bee Gees 的歌曲。這才是真正的恨啊。
你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吉他手、歌手和鼓手。我很好奇這些技能之間的遷移。前幾天,我在聽浪費光,你真正撕碎的地方。其中一些連複段看起來幾乎就像打擊樂模式。
我的腦子裡有一些交叉的線。因此,如果我唱歌,人聲的節奏將由與另一種樂器連結的模式決定。當我彈吉他時,我會像看底鼓一樣看低音 E 弦。我看著 A 弦,就像看小鼓一樣。我看著較高的琴弦,它們像鈸一樣響起。所以這一切都是相連的。我還認為構圖和排列就像時鐘中的輪子一樣。它很大而且在旋轉,然後它旁邊還有另一個小東西也在旋轉,它們一起旋轉。我記得第一次意識到齊柏林飛艇的「克什米爾」是兩個相反的拍號。我想,「這是數學。哇。
身為齊柏林飛船的超級粉絲,你是否會因為知道他們從像這樣的人那裡拿走了多少錢而感到困擾?威利·迪克森、穆迪·沃特斯和羅伯特·約翰遜,人們有時不得不提起訴訟以獲得適當的信用?
那是別人的訴訟,不是我的。
我換個說法:當我們談論垃圾搖滾的建築師時,我們談論的是 U-Men 和 Melvins。我們不談論蒂娜·貝爾等人。搖滾樂的故事僅限於講述的人。我很好奇你,作為一個除了音樂家之外還是紀錄片製作人的人,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索尼克高速公路並與巴迪蓋伊談論了他的開始和搬到芝加哥的經歷,他感謝我讓布魯斯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他擔心有一天憂鬱情緒會消失,所以他有點說,“繼續把它傳遞下去。”我一直對影響我的音樂持開放態度,我向所有教我如何演奏樂器的人給予很多支持。我一直很喜歡這些根的想法,這些根可以長成在未來幾年開花的東西,或是為下一代播下的種子。
我最近在重看《巴迪蓋伊》劇集時想到了這一點。在您的電影和電視工作中,您的意圖可能是為後代創造音樂史的記錄。
我為了那個系列訪問了一百個人。這是一部美國音樂史——不是故事的全部,但卻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常常想,「這是我的下一本書嗎?那是我的播客嗎?因為它需要被聽到,這樣人們不僅會欣賞我們所取得的成就,而且還會有所期待。我確實相信音樂的血統。美國音樂的演變,樂器、技術和創造力的演變。生命的目的是成長。我仍然相信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瘋狂的音樂世界是一個社區。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右邊有一支韓國流行樂隊,左邊有艾莉西亞·凱斯 (Alicia Keys),那麼我們就在一起了。在這個該死的時刻,噴火戰機可能就像克羅斯比、史蒂爾斯和納許一樣,但我們在一起。
幾年前,我一心一意想要建立自己的人脈。我他媽的瘋了。 “我要開辦自己的音樂頻道。”我的想法是音樂節目不應該只是視頻。它應該是更深入或更實質地介紹藝術家的東西,無論是現場表演還是迷你紀錄片。我和我的老朋友朱迪·麥格拉思 (Judy McGrath) 聚在一起,她很久以前曾負責管理 MTV。我們坐下來吃晚飯,她說:“我可以給你一個頻道。”我想,“真的嗎?” “是的。”然後她問:“你真的想成為電視主管嗎?”我當時想,「不,操那個。決不。他媽的沒辦法。
當你看到像這樣的退伍軍人時埃里克·克萊普頓 (Eric Clapton) 和範·莫里森 (Van Morrison) 大聲進行錯誤的鬥爭而失去劇情,你是否擔心很容易失去聯繫?是什麼讓你保持脈搏?
今天我和媽媽談論我是如何與文化脈動脫節的。我說:“嘿,你看過艾美獎嗎?”她說:“是的。”我說:“怎麼樣?”她說:“看看人們穿什麼很有趣,但我還沒看過任何演出。”然後我意識到我已經他媽五年沒看電視了。即使我去看節目,我也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的記憶已經滿了你早上醒來,穿上鞋子,然後嘗試走一條直線。就是這樣。
在過去的一年裡,您的雙搖滾大廳入選者史蒂夫尼克斯和尼爾楊有出售部分或全部出版權到他們的目錄。
哦,我們注意了。我認識所有賣掉他們的出版權的人。
你有沒有想過很多?你會考慮一下嗎?
我理解為什麼有些樂團會這麼做。一支年輕的樂團面臨著一場大流行病的停擺,他們可能無法渡過難關——也許這就是一個原因。也許您正處於職業生涯的某個階段,您不想再上路並在所有體育場和競技場中比賽,而您想騎車進入日落。也許這是一個原因。我還沒考慮過,因為我們還在做唱片和寫歌。我確信有一天我會到達那裡,在那裡我會說,「去他媽的巡演。拿著吧,夥計。我會把它賣給你。給我一個他媽的號碼。
去年夏天,當克里斯特·諾沃塞利奇稱讚川普的演講,然後又不得不反悔並解釋說,事實上他並不親法西斯時,你有何感受?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克里斯特不是親法西斯主義者。克里斯特是我認識的最富同情心、最有愛心、最聰明的人之一。我可以向你保證,諾沃塞利克不是川普的粉絲。
二月,你表達了複合的興趣他們是彎曲的禿鷹為另一張專輯。你有沒有關注過喬許·霍姆的虐待兒童指控本月?
我不能談論這個,兄弟。對不起。我不能談論這個。這是一個很難的「不」。
你會再剪一次頭髮嗎?
絕對-他媽的-絕對。我想要。我的孩子會說,「爸爸,不要。你太醜了。別剪你他媽的頭髮。我有這樣的習慣,我會用刮鬍刀刮鬍子
7號,然後我會讓它長出來。但我最終停了下來。
你最喜歡哪一個葛萊美獎?
哦,來吧。這就像挑選孩子一樣。我可能不得不說我、諾沃塞利克和帕特與保羅麥卡尼一起憑藉《別讓我放鬆》贏得的那一個。我最喜歡的三個人一起贏得了格萊美獎,這真是太酷了。
您對現代搖滾音樂的現狀有何看法?
我不確定「現代搖滾」是什麼意思,但有一些我真的很喜歡的藝術家,無論年輕還是年長,他們都在創作非常酷的音樂。當我聽一個神話記錄,我想,“這讓我大吃一驚。”有些東西是我喜歡的,有些東西是我迷戀的,米茨基就是其中之一。或者鳥和蜜蜂。我的意思是,你不會認為 Bird and the Bee 是一支現代搖滾樂隊,但天哪。我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好的樂團。這是我們的製片人格雷格·庫斯汀。這是格雷格和伊納拉,他們寫的歌是其他人不可能寫的。日本龐克搖滾樂團 Otoboke Beaver。觀看這段視頻,聽一首名為“別點燃我的火」。這會讓你大吃一驚,夥計。這是你見過的最激烈的狗屎。所以當然它就在那裡。它會成為明年葛萊美頒獎典禮的中心舞台嗎?誰他媽在乎?我每天都看著像我女兒維奧萊特這樣的人發現它,所以對我來說,她就是它所在的地方。
我認為你比許多同齡人更大膽地嘗試將工作和家庭結合起來。我知道你媽媽的名字和你孩子的名字您與他們合作過的專案。我沒有意識到你和 Violet 在專輯中翻唱了 X 的“Nausea”是什麼驅使我們學分不是原來的。
我和 X 有一個有趣的聯繫,因為我和鼓手有關係。直到 90 年代我才意識到這一點。我是聽 X 長大的。 他們來自俄亥俄州,我祖母曾經住過的地方。她的家人來自俄亥俄州。當地報紙上寫道:“洛杉磯朋克傳奇 X,在俄亥俄州演出。”上面列出了他們的名字。鼓手的名字是 DJ Bonebrake。他們都有龐克搖滾的名字。 John Doe、Billy Zoom、Exene、DJ Bonebrake。我有記錄。她剪下剪報並發送給我。她在 DJ Bonebrake 的名字下面劃了線,並說:“你可能和這個男孩有親戚關係。”然後它突然響起:我他媽的祖母的娘家姓是 Bonebrake。這是他的真名。
Bonebrake 家族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來到美國,從瑞士經過德國,然後來到美國。他們定居在賓州-俄亥俄地區。他們是門諾派。他們就像他媽的賓州荷蘭人,馬匹和平頂帽什麼的。我終於見到了他,事實證明我們真的有血緣關係。但無論如何,是的。所以當我和 Violet 一起錄製那個封面時,我想,好吧,她會喜歡這個的。她從 Joni Mitchell 到 Misfits、X、Stevie Wonder 到一些隨機的俄羅斯科技哥特狗屎來回跳動。她是你一生中聽過的最好的大學 DJ。
這封面上的紳士沒關係最近提出訴訟,指控其為兒童色情製品。你對此持什麼立場?
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談論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花太多時間思考這個問題。我和大多數人的感覺一樣,我必須不同意。我就說這麼多。
我能想起他四次重新創作了那張照片。如果這是一個問題,為什麼還要每五年重新檢視一次呢?
聽著,他有一個沒關係紋身。我不知道。
為我解決一個長期的謎團:為什麼庫爾特有時會把《Smells Like Teen Spirit》中的歌詞從“我們的小團體”改為“我們的小部落”?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打鼓,夥計。快點。我只是想透過演出!
為了清晰起見,本次訪談經過編輯和精簡。
1986 年至 1990 年間,格羅爾擔任 Scream 樂團的鼓手。 Nirvana 的第三張也是最後一張錄音室專輯於 1993 年 9 月 13 日發行。 《Rape Me》等歌曲也引起了爭議,柯本稱這些歌曲是反強暴的。 當 Grohl 第一次打電話給 Nirvana 的貝斯手 Krist Novoselic 詢問鼓手的工作時,Novoselic 說他已經聘請了西雅圖樂隊 Mudhoney 的 Dan Peters,他也是 Nirvana 的現場成員。諾沃塞利克後來打電話給格羅爾,建議他與科本談談——兩人顯然對從穆德霍尼偷走彼得斯感到內疚。幾週之內,戴夫搬到了西雅圖。 大約在 1993-94 年期間,科本兩度服藥過量,目前尚不清楚他能否成功。據記者邁克爾·阿澤拉德 (Michael Azerrad) 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在一次事件發生後,考特尼·洛夫 (Courtney Love) 發現他昏倒在浴室裡,臉色發青。紐約客。“她很害怕,”他寫道,“她向樂隊工作人員發出消息:收拾好設備——明天不會有演出,因為科特已經死了。” 顏色和形狀是 Foo Fighters 的第二張錄音室專輯,發行於 1997 年 5 月。 吉他手帕特·斯米爾(Pat Smear) 於1997 年離開噴火戰機樂隊,然後於2005 年以巡迴吉他手身份重新加入。 William Goldsmith) 從1995 年到1997 年與樂團一起演奏。 Sex Pistols 於 1976 年底與 EMI 簽署了唱片合約,幾週後,吉他手 Steve Jones 在一次褻瀆的、如今已成為經典的電視採訪中宣稱他們已經花掉了預付款。 EMI 於 1977 年初退出,樂團與 A&M 簽約,幾天後樂團就退出了舞台。第三家唱片公司維珍唱片公司隨後發行了樂團的開創性的——也是唯一的——錄音室專輯,別介意這些廢話,這是性手槍, 1977年秋天。 Sonic Youth 是最早為獨立藝術家開拓全國巡迴演出的樂團之一。該樂團於 1989 年與格芬子公司 DGC 簽約,當時現場沒有其他人關注任何主要唱片公司,因此他們帶著不太知名的樂團進行巡迴演出。紀錄片1991:龐克崩潰的一年講述了這個故事的一些內容。 根據格羅爾的說法,在恩尼克皈依宗教後,進行龐克搖滾巡迴演出並不利於他的生活方式。 「我認為他帶著一位贊助商一起巡演,是為了讓他與自己的新信念保持一致,」格羅爾說。 金匠將影片上傳到他的 Facebook 頁面聲稱第五張 Sunny Day 專輯被埋在“David Grohl 的襪子抽屜”中,這是指他的工作室。當人們要求澄清時,他有點反悔了。 葛羅爾摔斷了腿2015 年瑞典《噴火戰機》演出期間。 多年來,威斯特伯勒浸信會教堂(Westboro Baptist Church) 對噴火戰鬥機樂隊(Foo Fighters) 的多場音樂會設置了糾察線——從2011 年發布的同性巡演視頻《Hot Buns》開始,該影片展示了樂隊成員裸體在一起洗澡的畫面。 浪費光是 Foo Fighters 於 2011 年 4 月發行的第七張錄音室專輯。沒關係製作人 Butch Vig 在模擬設備上強調原始性能。 齊柏林飛船偶爾會在歌曲創作方面表現得快速而鬆散,讓他們插入和重新詮釋的民謠、搖滾和布魯斯藝術家感到沮喪。這種習慣導致了多年的訴訟。 1987 年,藍調傳奇人物威利迪克森因樂團抄襲他為《Whole Lotta Love》創作的歌曲而獲得和解。 噴火戰機:索尼克高速公路由 Grohl 執導,是 2014 年 HBO 的紀錄片系列。該系列節目透過採訪每個城市的傳奇人物,探索了美國八個文化中心的音樂歷史。該節目與 Foo Fighters 的第八張專輯同時創作,索尼克高速公路,樂隊在訪問的每個城市或附近錄製一首歌曲。 2020 年 12 月,艾瑞克·克萊普頓 (Eric Clapton) 和範·莫里森 (Van Morrison) 發行了《Stand and Deliver》 抗議英國的大流行封鎖規則。 2021 年 6 月,兩人再次合作創作了另一首古怪的歌曲《The Rebels》。 格羅爾和他的母親維吉尼亞·漢隆·格羅爾(主持人)從搖籃到舞台,Paramount+ 系列於 2021 年 5 月發行,靈感源自她的同名書。兩人訪問了音樂家和他們的母親。 2020 年 1 月,格羅爾當時 13 歲的女兒維奧萊特 (Violet) 與聖文森特 (St. Vincent)、貝克 (Beck) 以及 Nirvana 的倖存成員一起表演在子宮內搖滾天堂盛會上的「心型盒子」。 是什麼驅使我們是一部由 Grohl 執導的紀錄片,於 2021 年 4 月透過 Coda Collection 發行。它透過對 U2、Red Hot Chili Peppers、No Doubt、AC/DC、Dead Kennedys、Minor Threat、Foo Fighters 等樂團成員的採訪,探討了旅行車在搖滾樂歷史中的作用。
您透過我們的連結購買的東西可能會賺取沃克斯媒體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