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片:由霍珀斯通/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提供/亞馬遜工作室和路邊景點提供/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影公司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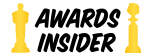
在這裡,八位頒獎季候選人分享了他們在銀幕上面臨的最大挑戰。
馬修麥康納在 金子
場景:麥康納飾演鬥志旺盛的礦業商人肯尼威爾斯,終於發了財。他的公司吸引了華爾街投資者的興趣,他們想買他的股份。在這一幕中,他必須做出選擇。
「當場景開始時,很明顯肯尼剛剛聽說這些華爾街的傢伙想買下他的股份。他看著合約:“我的名字在哪裡?”你想讓我成為少數股東嗎?所以我進入熱。我像一頭關在籠子裡的獅子一樣在房間裡來回踱步。衝突立即顯現出來,肯尼正試圖弄清楚該怎麼做。在我看來,他對獲得 3 億美元的報價感到興奮,事實上他的合夥人邁克·阿科斯塔並不在他身邊,然後這筆交易違背了他的原則 - 所以他很生氣。
這不是我可以重複20遍的場景。我會很累的。所以肯尼正在思考這一切,當他踱步時,我想到了那句台詞,他彎下腰說:“你要操我的屁股嗎?”這是我聽過的關於製片人迪諾·德·勞倫蒂斯 (Dino De Laurentiis) 的故事。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但我聽說他有權利沉默的羔羊他去工作室開會,他們說,“我們真的很喜歡這些書,我們想選擇它們,這是我們的報價。”迪諾只是認真地聽著,看著這個提議,站起來,脫下褲子,說出了我當時的即興想法。肯尼就是用這種方式告訴那些在東西上刻有自己名字的華爾街傢伙,他不會讓他們把他的名字從他的公司上除掉。他讓遺產得以延續。
我們並沒有真正規劃好那個場景,也沒有進行大量排練。我們曾經這樣做過,而且很有效,但後來飾演一位華爾街人士的寇瑞·斯托爾 (Corey Stoll) 對節奏有了自己的想法。我認為在第二次拍攝中,科里給我倒了一杯飲料——這是一件非常聰明的事情。所以他把飲料遞出去,就像,別吃蘋果,肯尼!不要這樣做!觀眾不確定肯尼要走哪條路。他是要拿錢還是要保持純潔?我在想,我該把這杯酒從他手中奪走嗎?它在這個本該瘋狂的場景中創造瞭如此美妙的中斷。然後,肯尼沒有把酒拍掉,而是接過它,一飲而盡——不是因為他背叛了自己,而是因為他正在為他即將要做的事情做好準備。就在那時,肯尼講述了科里的角色——他看著科里的眼睛,基本上說,「在我賣掉那家公司之前,我會殺了你,我父親親手建立了那家公司,」然後他走了出去。當肯尼說:『我的一天!我的一天!當他離開時,我也加入了一些東西。整個場景寫得真好,動態清晰,衝突清晰,選擇明確,展現了肯尼近乎孩童般的純潔。他和我打過的任何人都不一樣。
加奈爾·夢奈在 隱藏人物
場景:隱藏人物是三位開創性黑人女性的故事他在 20 世紀 60 年代擔任 NASA 工程師。在這個場景中,夢奈扮演的角色瑪麗傑克森不得不向一位不情願的法官請求允許她在一所全白人學校參加她需要的高級課程。
「事實上,我必須試鏡這個場景。這是導演希望我完成的場景。他要我進來時已經準備好了。當我讀到這個劇本時,我一直在想的是,這是一個夢想的角色。瑪麗傑克遜希望為自己和她的同齡人伸張正義。我對她負有個人責任,要尊重她,所以我非常認真地對待它。我想到了所有像我祖母這樣的女性,以及所有為我打開大門的女性,尤其是在那個時代。我想到了他們,想到了我必須非常聰明並且對我的語言非常挑剔。因為加奈爾·夢奈當時可能會有不同的措詞。我們現在有言論自由,但當時那些女士沒有。他們的兄弟姊妹因為他們看待白人的方式以及與白人交談的方式而被私刑處死。所以我必須對如何扮演瑪麗非常有策略。法庭上確實是走鋼索。但她最終獲勝了。
對我來說,來自音樂方面,我想進入音樂產業並重新定義作為非裔美國女性唱片藝術家的意義。我想重新定義性感的意義,並且不扮演任何刻板的性別角色。所以我把這一點帶到了[這個角色],因為我覺得我做了一些與她在那個時代會做出的選擇相同的選擇,而且我覺得我們絕對是志同道合的人。我立刻感覺到與她的連結。當我準備這個角色時,我用它作為燃料。而且因為我必須前後了解這個場景,所以拍攝這個場景我其實是最輕鬆的。對我來說,我有機會真正發揮它,發揮作用並允許靈感以及別人看待我的方式給我另一種方式來表達某些事情。我記得拍了兩次,[導演西奧多·梅爾菲]說,『我們有基礎了。我們有我們需要的東西。現在我們就來玩吧。我當時想,“真的嗎?”我很震驚。我當時想,“你是認真的嗎?”他說,『是的,我們有。那很棒。現在就這樣玩吧。
[弗蘭克·霍伊特·泰勒,扮演法官]是個甜心,但當我見到他時,他的個性非常好。他給了我很多工作要做。我終於可以和我的敵人面對面了。但後來他握了我的手,我想我們甚至可能一起流淚了,因為那個場景對每個人來說都很感人。當鏡頭停止轉動時,每個人都淚流滿面。我記得我轉過身來,所有的髮型師、化妝師、攝影指導,我記得他們走過來對我說:“我們拍了很多場景,但這很特別。” [弗蘭克]真是個可愛的人,他擁抱我說:『恭喜你。你將觸動世界各地的心。我說:“我希望如此。”我真的希望瑪麗的精神能夠繼續下去,人們能夠受到她的啟發。
傑夫布里吉斯在地獄還是高水位
場景:布里奇斯飾演德克薩斯遊騎兵馬庫斯漢密爾頓,他一直在追蹤一對實施了一系列大膽銀行搶劫的兄弟。在這一幕中,他終於面對了他的獵物托比·霍華德(克里斯·派恩飾)。
警告:劇透!
「你知道,我非常不願意談論這個,因為這有點像魔術師洩露他的魔術技巧。我不希望人們在觀看電影時考慮我的方法,但我可以說那個場景中有很多東西可以發揮。我的角色正在經歷很多不同的事情。他必須面對退休的問題。然後他的朋友和搭檔被托比的兄弟殺死了。因此,當他決定去探望托比時,他的怒火就起來了。但他也很好奇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托比為什麼要做這一切。
當他到達那裡時,他不想因為生氣而毀掉他的偵探工作,而且由於他們都有槍,他不想自己被殺,也不想殺了那個人。在這樣一個充滿張力的場景中,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只是停留在寫作上。已經很緊張了。想太多或嘗試做太多都會把整件事情搞砸。你只需要演他媽的場景,知道嗎?在那一刻就作為角色在那裡。
那天我們很幸運有一位著名的德州遊騎兵華金傑克森在片場。我從他那裡得到了很多。當我坐在門廊的椅子上,脫下帽子並將其掛在靴子上時,華金就是這樣做的。他的存在浸透了我。你認為這樣的壞蛋會很難對付,但他卻有一種真正的甜蜜和紳士風度。當托比的家人出現在這個場景中並且馬庫斯非常有禮貌時,你會看到這一點。就在那時,他說出了「你為孩子做的事情,嗯?」這句話,這是整件事的關鍵。
克里斯和我排練了很多次那個場景。我喜歡穿著戲服排練,盡快脫離劇本,這樣我才能真正融入角色。大衛麥肯齊是那種不會告訴你太多的導演,所以你只是把所有的原料放在一起燉,看看結果如何。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你可以提前想好這一切,你要怎麼做,但一旦你到達現場,你就放手去詢問精神,偉大的實體,'跟我做你想讓我做的事。所以在這個場景的一些鏡頭中,“也許把你的重量放在椅子上的另一隻手臂上。”或“注意你手中啤酒的冰涼程度。”像這樣的小事就可以讓我在電影中的這個時刻進一步了解馬庫斯。
這個場景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就是它的模糊性——關於對與錯以及誰將對誰做什麼。有句台詞是,當馬庫斯離開門廊時,托比告訴他,他們可以找個時間談談,他說,「也許我會給你一些平靜,」馬庫斯說,「也許我會給你平靜。我用手指在空中輕輕揮了一下,這也是我從華金身上學到的。但電影結尾處關於給予彼此和平的問題——我們人類,我們尋求並渴望和平,但我們是如此暴力的物種。你如何協調這一點?你只是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尋找答案。
米歇爾·威廉斯在 海邊的曼徹斯特
場景:威廉斯飾演李(凱西阿弗萊克飾)的前妻,在一場痛苦的對抗中,她試圖向她受傷的前夫伸出援手,但他不會——或者不能——接受她的橄欖枝。
「那個場景感覺有點像處決日:它即將到來,即將被拍攝,但你卻無能為力。我們確實得到了幾次赦免,因為我們應該在實際拍攝之前拍攝該場景兩次,也許三次。由於製作方面的困難,我出現在波士頓並被告知,『我們今天不打算這樣做。你可以回家了。每次,我都會結合深度釋放和,好吧,我該怎麼辦這一切呢?因為在這之前的一週裡,我一直在情感和心理上非常仔細地做好準備。
這一天終於來了。這幾乎是拍攝的最後一天了——確實不能再推遲了。您知道生活中的那些時候,當您意識到這是您第一次或最後一次要做某事時,周圍的一切都變得非常充滿活力?這就是一整天的感覺。我記得我穿好衣服了。我記得在我的蜜車裡等待,那是一種監獄牢房,他們在獨立電影中關你。我記得我在化妝。我記得我正在聽的歌曲。我記得走上階梯的情景。技術上有很多事情要做好,情感上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好。
我認為我和我的角色蘭迪在那個場景真正發生之前已經想像了一千次。由於對話重疊,這是一個非常需要學習的技術場景。 [導演兼編劇肯尼斯·洛納根]的眾多天才之一是他的寫作方式就像人們說話的方式一樣。它給人一種非常自然的感覺,但事實上一切都是放置的,這些重疊確實至關重要,如果你不能和某人一起運行場景來學習它的節奏,那麼它們就很難獲得。但我們沒有排練。我想我們誰也不想這麼做。我會說,’嘿,我們真的應該運行那個場景,因為,你知道,它真的很複雜。但我認為我們和角色本身對此有同樣的感受——我們有點想這樣做,但我大多數人真的不想這樣做。這根本不是[凱西]和我真正合作過的事情。我們分別進行了工作,然後我們在擂台上相遇了。
後來,我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感到鬆了一口氣,一切都結束了。我知道,在場景本身內部,我感受到了某種我以前在電影中從未體驗過的靈活性。所以這很令人興奮。但我離開片場時一定不會想,我做得很好,那將是一個很棒的場景。當你表演戲劇時,你可以知道什麼時候你贏了,什麼時候輸了,觀眾什麼時候支持你,什麼時候不支持你。但在電影拍攝現場,你回家時會有點困惑。喜歡,那是什麼?我希望一切順利。但我不知道。」
約翰·阿德波柵欄
場景:阿德波飾演科里,前棒球運動員特洛伊(丹澤爾華盛頓,他還執導了這部改編自奧古斯特威爾遜標誌性戲劇的電影)的兒子。在這個場景中,兩人之間長期存在的緊張關係最終演變成肢體衝突。
「丹澤爾絕對是我的英雄之一。在我們工作的第一個月,我很難把這個元素從我的工作中移除。每次他走進來時,我都會給自己五到十分鐘的時間,天哪,這是丹澤爾。那我就得暫停了。電影結尾的那場大戰對我來說無疑是最具挑戰性的──那場激烈的戰鬥。就丹澤爾的方向而言,這是多種因素的結合。在排練過程的早期,丹澤爾會提到這樣一個事實:電影接近尾聲的場景有很多感人的部分——但最要記住的是,這是父子之間衝突的高潮。所以在排練的時候,他會強調空間的重要性;當我這麼說時,我指的是劇場中的戲劇與電影中的戲劇。當你在舞台上表演衝突場景時,你可以向觀眾表演,並在某種程度上逃避你和場景搭檔之間的衝突。而在電影中,你無處可去。這將是持續的目光接觸。有時你可能會看到我在爭吵時向他邁出一步。然後,如果他對我說了些什麼,而我感到受到威脅,我可能會後退一步,而他會向前邁出一步。這幾乎就像一場舞蹈——就像一場拳擊比賽的編排。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奧古斯特威爾森的話已經非常富有詩意了。你幾乎可以對它們打響指。這是我們在整個場景中都非常注意的事情。
丹澤爾還得不斷提醒我放慢語速。當我真的很興奮的時候——當 Jovan 真的很興奮的時候——我往往會說得很快。我的大腦思考得太快了。所以他會說,“慢點,慢點,慢點!”奧古斯特·威爾森在故事中寫下的文字與說話的語氣一樣重要。所以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丹澤爾會提醒我,『我知道科里在這裡很生氣,我知道你很熱情,這是一個重要的場景。但請確保您慢慢來。並確保你能理解科里的觀點,因為如果你太專注於當下並且只是脫口而出,你可能會錯過對場景很重要的戲劇性節拍。如果你正忙著說話和說話,你可能會直接跳過它。
丹澤爾想讓我們感受到特洛伊和科里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們之間的對峙是不可避免的:在每個小男孩生命中的那個時刻,他必須成為一個男人。
菲麗希緹瓊斯在 怪物召喚
場景:瓊斯飾演一位患有晚期癌症的單親媽媽和一個難以理解癌症的小兒子。在這個場景中,瓊斯扮演的角色莉齊必須幫助她的兒子麵對真相,儘管她意識到自己也必須面對它。
「最困難的場景是電影接近尾聲的場景。我的角色必須真正面對她即將死去的事實,而這是她一直在逃避的事情。她不想承認。她試圖盡可能保持堅強,她不希望她的兒子不得不面對這一切。你知道,他們的關係非常特別。她是一位單親家長。她很小的時候就有了康納。所以她自己也差不多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她仍然有一種叛逆的精神,一種叛逆的特質,他們成長過程中更像是朋友,而不是嚴格的父母關係。
因此,當那一刻到來時,她最終必須相信她給他的一切,並相信他自己會好起來的。而且她很難放手。在片場,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場景。從某些方面來說,扮演一個正在戰鬥的人要容易得多反對某物。但就在這一刻,一分錢都掉了。她必須對兒子非常坦誠,這在某些方面是最難做到的。
傑西卡·查斯坦在 斯隆小姐
場景:查斯坦飾演殘酷的遊說者伊莉莎白史隆,她試圖推動槍枝管制法案的通過。在這一高潮場景中,她被拖到國會委員會面前解釋自己的情況,然後她陷入了最後一個陷阱。
「那是在經歷了非常艱難的一周之後。我想在拍攝這個場景的前一周,我們拍攝了 24 頁,這是我以前從未在電影中做過的。我們拍攝得非常快,並試圖拍攝很多頁面,我記得我說,“你們這些傢伙,我感覺我要崩潰了。”我認為這一幕是在那之後發生的。
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需要做這麼多準備的情況。術語需要如此具體和快速。這是[導演約翰馬登]一直在談論的事情,關於她的節奏需要多快。從電影一開始,我們總是看到伊莉莎白在忙碌。她正在前進。如果她是一隻動物,她就會是在水中的動物——她總是以這種非常流暢的方式前進,但速度非常快。然後在這個場景中,我記得約翰一直試著讓我慢下來。他說:“坐在那裡吧。”當我們完成後,他說,“好吧,我很好,”我說,“呃,我可以再做一次嗎?我可以做得很快嗎?”他要我這麼做,但他沒有使用那個鏡頭。他對她真正在場很感興趣,我很高興。你知道,我兩天前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的完成狀態,我真的能感覺到她在最後的時候是多麼的疲憊。我能看到這一點,而且我認為他為那個場景給了我很好的指導。
每當我閱讀任何劇本並想弄清楚它是否是我要參與的內容時,我都會嘗試感受角色的想法。我不會大聲說出台詞,但在情感上我完全遵循這個故事。我確實把自己置於這樣的境地。我正在讀一些東西,看看我是否會允許這個角色進入我的生活——我是否能理解他們,即使他們做了壞事。如果我能與這個人達成一些理解,即使他們與我有很大不同。對我來說,這會說,好吧,我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是的,這是我可以扮演的角色。如果我讀了一些東西然後我就走了天哪,這個人的行為太反常了,當他們這樣做的原因甚至沒有書面理由時,那麼這不是我可以玩的東西。我非常注重細節和具體。
而且,在這部電影中我總是很累。我的意思是,我在多倫多,我一個人,沒有人陪我。通常我會和家人一起旅行,所以我從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孤獨的人,但對於斯隆我沒有那個。這不是故意的。我並不想成為「Method-y」。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我真的很感激它就這樣發生了。因為我會完成一天的拍攝,然後我必須回家,吃晚飯,然後我會開始記住第二天的五頁獨白或任何我擁有的東西,這,如果你看劇本,你會發現這是一系列一遍又一遍的獨白。這其中有一些如此孤獨和沮喪的東西,但它們是幸福的意外。我只是在扮演角色時利用這種感覺。
休葛蘭在佛羅倫斯·福斯特·詹金斯
場景:在史蒂芬弗雷爾斯這部關於一位不會唱歌的歌手(梅莉史翠普飾)的喜劇中,休葛蘭飾演詹金斯的男友聖克萊爾貝菲爾德。在電影的結尾,當史翠普扮演的角色瀕臨死亡時,格蘭特必須表達他深深的感情,然後情感崩潰。
「當我第一次拿到劇本時,我正在閱讀劇本並想,這太棒了。我也許能做到這一點。然後我到了弗洛倫斯去世的部分,劇本上寫著:“貝菲爾德無法控制地抽泣。”我在旁邊畫了一個小問號。無法控制地抽泣是一件很難受的事情。我從來沒有實現過。在我簽約這部電影後,我有一年的時間擔心不能在梅莉史翠普面前哭泣。然後機緣巧合,臨終哭泣的戲被安排在拍攝的最後一天,所以整個拍攝過程中我也不得不害怕哭泣的戲。終於有一天,我想,我將在梅莉史翠普面前以輕量級的身份亮相。所以我坐在我的小更衣室裡,做了演員應該做的事情,走進了我生命中所有最悲傷的地方,戴上耳機,聽著悲傷的音樂,一個叫做「軍人妻子合唱團」的團體,我在想,我還不夠難過。然後有人過來告訴我該去片場了,我坐下來,這是我的特寫鏡頭,我歇斯底里地哭了起來。我的意思是,我的眼淚從耳朵裡湧出來,鼻涕從鼻子流到梅莉史翠普的手上。後來,我感到很沾沾自喜——這是我在電影片場感受到的最快樂的事情,想到,我做到了!我哭了!然後,在剪輯過程中,史蒂芬·弗雷爾斯認為沒有眼淚的場景會更悲傷,因為如果演員哭了,觀眾不會。他是對的,但我很沮喪。所以我們重新拍攝時我只是感到悲傷,而不是哭泣——這也不容易。梅莉爾在拍攝初期就對我說,演員有責任在每個場景中表現出情感:如果這是一個悲傷的場景,就要真誠地悲傷,這讓我嚇壞了。沒有人比她更擅長這一點,而努力做到這一點並不是自然而然的事。這是一種非常美國化的電影表演方式,相信鏡頭最喜歡的是情感。梅莉爾總是說人們記得的是他們所看到的情感,而不是台詞。我的表演更多地與輕喜劇有關,這確實有技術方面的問題。有些節奏和重音會讓台詞變得有趣,而有些節奏和重音則不會。情緒較沉重的場景則不然。但是,看,佛羅倫斯·福斯特·詹金斯死亡場景是關於愛的。佛羅倫斯和貝菲爾德彼此深愛,儘管他們的戀情形式很奇怪。所以讓我哭泣的是對愛情的思考。因為我確實了解愛——上帝啊,我聽起來簡直就是個演員的混蛋——但無條件的愛,尤其是在疲勞或壓力的適當狀態下,會讓你哭笑不得。秘密是如果沒有我的孩子我就不可能完成那個場景。尤其是人到中年,愛情讓我流淚。我為我對孩子的愛和孩子對我的愛而感動。我已經變成一個可怕的老軟蛋了。這就是這個場景中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個死亡場景,但它實際上並不是一個悲傷的場景。
*本文發表於2016年11月28日號紐約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