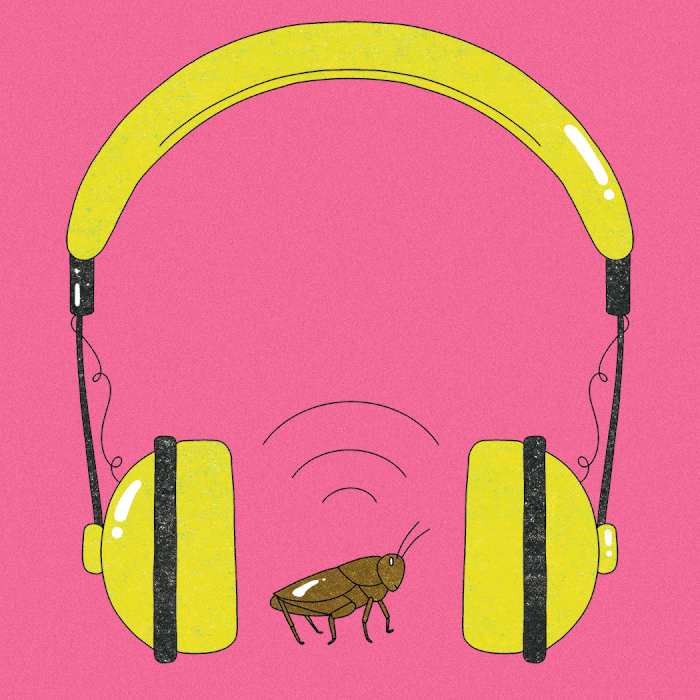
這篇文章被推薦於一個偉大的故事,紐約的閱讀推薦通訊。在這裡註冊每晚得到它。
今年九月的一個星期一,巴爾的摩的一位法官提醒擁有耳機的公民,播客曾經很強大。她的裁決——撤銷對一名被指控謀殺高中女友的男子的定罪——可以直接追溯到 2014 年的熱門歌曲序列,這使得這起懸而未決的案件每週都引起全國越來越強烈的關注。當節目首次亮相時,播客主要是聊天廣播和回收廣播的數位死水。突然間,有序列話語,一個週六夜現場短劇和聆聽派對直接來自聚集在留聲機時代。 「這感覺真的很令人興奮,」當時擔任文學經紀人助理的喬伊·福克斯 (Joy Fowlkes) 說。 “就像我很早就開始做某事一樣。”
播客已經在慢慢走向相關性,但是序列短短七週內下載量就達到 1,000 萬次,一躍成為主流。已故大衛卡爾的紐約時代 關於這一現象的專欄標題為「突破性播客為更多內容奠定了基礎」。接下來是一個豐富的創意時期,以一系列熱門節目為標誌——讓我們稱之為“大片”播客——在引發全國性對話方面堪比好萊塢和圖書出版。很多,例如序列,是雄心勃勃的限量版敘事項目。在理查德·西蒙斯失踪,一位具有諷刺觀察天賦的前電視製片人正在尋找這位隱居的健身偶像;它足夠大,值得報道次,一位評論家稱其為“最新的聲望播客痴迷”並譴責其策略。異想天開神秘表演贏得斯塔莉·凱恩出現在柯南。而在2017年,序列的製作公司發布S鎮,一部近乎反商業的文學非小說類項目,講述了一個不起眼的人的非凡生活。它很快就引起了轟動,出於文化義務,你不得不聽它,它讓你想知道下一個節目會實現這一壯舉。
誠實地?很難說有哪一個有。
已經過去快八年了序列掉了。整個產業蓬勃發展,吸引了好萊塢製片廠、企業、名人和數十億美元。但轟動一時的播客——對於該媒體作為一種藝術力量的崛起至關重要的子流派或聲望層——卻陷入了嚴重的恐慌之中。我確信你的手機充滿了播客,也許你已經說服了一位朋友將你的最愛添加到他們的隊列中。但是,你認識的每個人最後一次剖析單一標題是什麼時候?
對一些業內人士來說,媒體推動這類時刻的能力不斷減弱,帶來了生存問題。如果播客很少引起廣泛的批判性討論,那麼它對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播客意味著什麼? 「讓我這樣說:熊很受歡迎,」福克斯(現為格納特公司的播客人才經紀人)在談到今年夏季的突破性電視節目時說道。 「這是在談話中。目前播客中的任何內容都不會在已經收聽過播客的人們的範圍之外產生任何影響。
有時,您肯定聽過的笑話——現在每個人都有播客——開始感覺真的是真的。 Apple Podcasts 列出了 250 萬個節目; Spotify 聲稱數量是其兩倍。該領域的數據是出了名的參差不齊,但將其放在上下文中:序列Libsyn 首播時,當時最大的播客託管平台之一,僅支援約 22,000 個節目。馬克斯林斯基 (Max Linsky) 是菠蘿街工作室 (Pineapple Street Studios) 的聯合創始人,這家商店製作了失蹤理查德·西蒙斯,相信這種指數級成長對敘事類遊戲來說是一種獨特的劣勢。 「和西蒙斯,我認為在這六週的時間內不會推出太多的限量播客(如果有的話),」林斯基說。 「現在,每天都會有一個新的、雄心勃勃的人出現。想要到達一個有很多人同時收聽的地方就更困難了。
擁擠的市場幾乎讓所有業務都變得更加困難。蘋果播客應用程式上的空間有限,其圖表和編輯頁面是觀眾可以可靠地發現新節目的少數空間。這種擁擠也擴大了現有企業與外部企業之間的差距。較大的出版商通常會建立播客源,透過它們可以宣傳新版本;較小的工作室通常不會。與此同時,播客行銷的成本正在上升,這仍然是一種新生的做法,一些出版商現在願意花費六位數在其他播客、社交媒體、網站甚至戶外廣告看板上做廣告。
「當我們在 2018 年剛開始時,我們可以推出一個沒有大名鼎鼎的節目,透過 Apple 播客上的一些宣傳片、少量的媒體宣傳和口碑相傳,每集獲得約 30,000 次下載,」Shira 說獨立工作室Wonder Media Network 的阿特金斯。 “今天,如果我們不投入大量的行銷預算,這幾乎是不可能的。”該工作室最近發布了我從來沒在那兒,一個在內部被認為不太受歡迎的敘事播客。它被選入今年的翠貝卡音樂節,並躋身蘋果播客排行榜的前列。但是,阿特金斯告訴我,“我們只是在這個節目上賠了錢。”
一些製片廠現在將業務定位為向好萊塢出售電影和電視版權,但許多創作者仍然依賴廣告,這種方法強調純粹的數量:更多季節、更多集數、更多庫存。這兩種模式都在與所謂的「永遠在線」播客的戰鬥中失敗,這種播客是基於對話和採訪的節目,製作成本更低,並且隨著其過往目錄的長尾增長而變得更加強大。我從來沒在那兒上線幾週內下載量就超過 10 萬次。但叫她爸爸據報道約有 300 萬聽眾,且喬羅根曾聲稱他的名人雲集的節目每月下載量約為 1.9 億次。
「我們喜歡出版限量版節目,」iHeartMedia 播客網絡的首席營運長 Will Pearson 說,該網絡資助了廣受好評的小型敘事項目,例如傑米·洛夫特斯的洛麗塔播客 和克里斯·斯特德曼的未讀 以及數百個聊天廣播。 “話雖這麼說,為了這項業務的長期穩定,我們希望建立盡可能廣泛的節目名單,每月下載量可以超過一百萬次。”
高層表示,這些都是成熟業務中的自然轉變,並且可以降低任何一場演出的風險。 (對於雄心勃勃的工作,這種風險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是聲譽上的。時代演出時很尷尬哈里發國原來是根據一位寓言家的敘述而寫的全部回覆關於種族偏見的系列享受你的食物引起了人們對播客自身盲點的強烈關注。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的修正主義歷史,播客行業的當前形態與她之前工作過的圖書出版業進行了比較。 「你擁有轟動一時的書籍水平:一些東西問世、佔據主導地位,並成為談話的中心——小龍蝦唱歌的地方,例如,」費恩說。 「但在這之下,還有另一層項目,這些項目是有利可圖的並且有觀眾。也許不是每個人都聽說過它們,但它們仍然很成功。
可能是這樣。但是當播客停止製作時會發生什麼小龍蝦?
今年早些時候,Serial Productions 的執行編輯 Julie Snyder 與 Gimlet Media 的聯合創始人 Alex Blumberg 共進晚餐,Gimlet Media 曾經是播客業務的金童,於 2019 年被出售給 Spotify。一樣消失嗎?
換句話說:媒體業務主要圍繞著高調的談話人物。廣播電台的拉許林博和霍華德史特恩;喬·羅根(Joe Rogan)、亞歷克斯·庫珀(Alex Cooper) 以及威爾·阿內特(Will Arnett)、傑森·貝特曼(Jason Bateman) 和肖恩·海耶斯( Sean Hayes 三人組(據報導與亞馬遜簽署了價值高達8000 萬美元的協議)從事播客業務。 「我確實知道現在的聽眾總體上要大得多,我想我們現在處於一個更小眾的類別,」史奈德說。 “但我們不想成為藝術之家,你知道嗎?”
Serial Productions 絕對不是藝術工廠,但與序列的第一季和S鎮,工作室的新作品感覺不像是即時的文化現象。特洛伊木馬事件,它的最新項目在前三週半內就獲得了超過 1300 萬次下載。S鎮第一個月就有 4000 萬。即便如此特洛伊木馬受益於時代(於 2020 年收購了 Serial Productions)並擁有更傳統的掛鉤——對英國重大政治醜聞的調查。 “S鎮沒有大的類型推動或大的謎團,」斯奈德說。 「這非常有藝術氣息,而且做得非常非常好。我確實想知道是否S鎮今天出來了,性能也一樣嗎?我真的不知道。
一些內部人士認為,可能永遠不會再有第二次了序列又是這樣的時刻。敘事播客工作室 Neon Hum Media 的執行編輯凱瑟琳·聖路易斯 (Catherine Saint Louis) 表示:“期望有一個我們所有人都想收聽的主流播客的想法有點愚蠢。”同情之痛和奇觀,除其他外。 “這就像問,’為什麼不再有預約電視了?’”
當高層和製片人談論蓬勃發展的播客市場時,經常會引用巔峰電視的比喻。考慮如何黃衫軍,第一季的大結局吸引了大約 130 萬觀眾,儘管觀眾數量明顯少於其他節目,但仍被認為很受歡迎。黃石公園,第四季結局的收視率超過 930 萬。這部青少年食人劇被廣泛認為是成功的,因為它在評論家和影響者中達到了臨界質量,同時服務於 Showtime 的商業目標。聖路易斯認為,播客還沒有一個社交基礎設施——一個由投入的受眾、品味創造者和媒體組成的內部推動網絡——能夠支持我們如何談論成功的音頻製作的那種微妙的反饋循環。
並不是所有人都認為病毒式傳播和轟動一時的地位從根本上來說很重要。一位業內人士表示:“與幾年前相比,現在聽各種音樂的人多了很多。” “他們可能只是不會和你的編輯一起去酒吧。”這可能是真的。畢竟,播客受眾群體整體持續成長。但如果幾乎沒有人在談論同一件事,就很難鞏固媒體的身份、文化和意義——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會對業務產生重大影響。 「輿論很重要,」愛迪生研究公司總裁拉里·羅辛說,該公司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播客領域。 “當然,有很多新節目很受歡迎,而且做得很好,但這個領域需要有全新的想法,讓人們想要回到播客或第一次嘗試。”
一些高層認為,播客近年來引起了廣泛關注。能量只是來自聊天廣播。人氣飆升少聰明,阿內特-貝特曼-海耶斯的鬧劇經常被作為一個例子,其親密的名人採訪經常成為娛樂行業出版物的頭條新聞。我採訪過的一些業內人士提到了傑米·林恩·斯皮爾斯 (Jamie Lynn Spears) 最近在叫她爸爸作為節目的突破時刻;其他人指出喬羅根的經歷是文化戰爭的頻繁前線。但這些例子植根於名人的可替代力量。播客本身對於這些企業來說是附帶的;主辦單位可以輕鬆地將他們的業務轉移到其他媒體。
如果播客如今受到關注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其傳播具有新聞價值的八卦或擴展各種一線明星、公眾人物和潛在影響者品牌的能力,這意味著什麼?正如斯奈德所擔心的那樣,這意味著播客已經或將變得與企業廣播沒有區別。這將是一種恥辱,因為播客八年前爆炸性地進入主流主要是由這種媒體作為藝術的可能性所定義的。
如今,“沒有人願意冒任何創意風險”,曾在多家大型出版商工作過的資深播客高管兼製作人勞拉·梅耶爾 (Laura Mayer) 說。 “我們看到很多人都在努力對播客的成功進行逆向工程,因此,我們在卡拉 OK 領域做出了很多對過去成功的嘗試。”
媒材成為藝術形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內在趨勢和運動的存在:序列推動了真實犯罪播客的整個生態系統,艾拉·格拉斯(Ira Glass)激勵了一代以某種方式寫作和聽起來的敘事製作人。保持藝術形式活力的是不斷的有機重塑——也就是說,媒介有能力培養、吸收並透過新想法進行改造,這些新想法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上,並對前人提出質疑。鑑於該行業對名人演員陣容的執著以及將真實犯罪研究外包給維基百科的習慣,很難說播客最近做了很多改造。
這只是理性的,因為盛行的、廣告驅動的商業模式不會激勵創造性的賭博。訂閱模式帶來了一些希望,在這種模式下,有直接的經濟誘因來支持大幅波動並嘗試未經考驗的人才。幾年前,一家名為 Luminary 的新創公司試圖抓住這個機會,但基本上未能實現。現在包括 Wondery 和索尼音樂娛樂在內的主要發行商都在嘗試透過蘋果和 Spotify 建立訂閱服務。亞馬遜的有聲書子公司 Audible 正在與著名的播客創作者合作。它最近與背後的二人杰弗裡·克蘭諾(Jeffrey Cranor)和約瑟夫·芬克(Joseph Fink)簽署了協議歡迎來到夜谷,以及 Prologue Projects,該工作室由緩慢燃燒的 Leon Neyfakh,製作原創項目。問題是 Audible——傳統上更像是零售商,而不是創意工作室——是否真的有能力推出大片。即使是 2018 年與該公司簽署多年協議的非小說類大神邁克爾·劉易斯 (Michael Lewis) 的音頻作品也沒有引起太大的狂熱。
Serial Productions 的 Snyder 和 Pineapple Street 的 Linsky 等資深人士提醒我,播客還很年輕。 「五年前,根本沒有那麼多演出,」史奈德說。 「而且工作崗位也不多。你知道,這件事真的很難做到。我們對此都很陌生。所以,當然,今天,好東西可能感覺越來越少,而且相隔很遠,因為我們都還在進步。林斯基相信我們再次看到熱門歌曲只是時間問題。 「讓我樂觀的是,播客作為一種形式越成熟,就越多的年輕人和那些現在不認為自己是這類節目創作者的人會認為這是一條可行的道路,」他說。 “他們會對這些節目如何聽起來、如何製作以及如何吸引人們收聽有不同的想法。”
不過,播客目前並不缺乏有價值的人才。考慮大西洋報的洪水線該計畫從 2020 年開始,實現了聲音設計的驚人願景,同時對政府在卡崔娜颶風中的失敗進行了重新訴訟。或實驗性的元小說莎朗·馬希希的出場次數。或是傑米·洛夫特斯 (Jamie Loftus),她是當今媒體界最令人興奮的獨立創作者,她對龐克搖滾的好奇心與日俱增。人才不是問題。圍繞它的激勵結構正在改變。
也許播客大熱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播客在這種損失中並不是獨一無二的——畢竟,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一切都太多的後單一文化時代。也許安於藝術之家並不是那麼糟糕:行業內一個較小的領域,用於新想法、新人才和真正的播客作為播客。會有很多東西填滿你的耳朵。只是不要指望在聆聽聚會上聽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