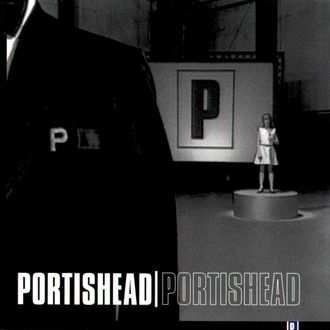
最初的三人組合於 90 年代初聚集在布里斯托爾,後來不情願地以“trip-hop”的名義組合在一起,這絕非偶然。儘管Massive Attack、Tricky 和Portishead 的聲音永遠不會被誤認為彼此,但這三人有很多共同點:對女性聲音的可能性的持續興趣以及對黃金時代美國說唱的熱愛,尤其是Public Enemy ,他們透過同樣沉重但明顯不那麼喧鬧的音景傳達了堅定不移的政治態度。也有個人關係。藍線,Massive Attack 的首張 LP,不僅對於以 DJ 3D 和 Daddy G 為中心的樂團來說是零基礎,而且是技巧,他的幾首精彩的客串詩是他天才的第一個跡象,他的處女作傑作是超密集、淫蕩的壓力。Maxinquaye。同時,傑夫·巴羅 (Geoff Barrow) 是一位年輕的音響工程師,他致力於藍線Massive Attack 給了他一個空閒的錄音室時間來嘗試自己的樂器。
當巴羅遇到了貝絲·吉本斯(Beth Gibbons)時,這份禮物得到了充分的回報。 。不久之後,擁有豐富爵士樂隊演奏經驗的吉他手阿德里安·烏特利(Adrian Utley) 加入進來,他們的合作發展成為一支奇怪的樂隊——製作人DJ Barrow 佔據了傳統上由鼓手和貝斯吉他手佔據的空間——他們將其命名為Portishead,以紀念該地區的沿海小鎮。由EP (麻木感)和短片(殺死一個死人)他們為 Portishead 的第一張專輯執導並創作了配樂假的(1994)受到英國大眾的熱烈歡迎。清脆的樣本和碎拍、海洋般的貝斯、沉思的吉他線以及吉本斯溫柔而水晶般的表達的完美結合,假的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彷彿長久以來的某種深奧的潛力終於得以實現。大多數首張專輯都展現了藝術家們正在發現自己的能力。假的適應這個模式,同時深化它:歌詞和聲音似乎不僅至關重要,而且是有感情的和自我反省的,能夠使一個人自己的發現過程成為主要主題。 「你知道沒有人能看到你的視野嗎? /你意識到裡面的世界是屬於你的嗎?吉本斯在《陌生人》中演唱,她的聲音充滿了極度平靜的活力。
聽假的就是聆聽吉本斯將自己完全交給樂團成員的聲音,同時又以某種方式完全凌駕於其之上。她的歌詞充滿了一種罕見的良知感,或者是一種等待其適當對象的信仰:“愛並不總是閃耀。”有時,她的確信甚至可能被認為是說教(「我們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認識到錯誤」),但即便如此,佈道的講道也沒有誇張,而是帶有一種可以被可信地描述為文學的感性。吉本斯在《流浪之星》中的副歌暗指《新約全書》中的一個深刻的切口,與詹姆斯國王翻譯中的一首詩相匹配(猶大書 1:13)幾乎逐字逐句:“流浪的星星,永遠為他們保留著黑暗的黑暗。” 《猶大書》這節經文的前面是「大海的洶湧波浪,吐出他們自己的恥辱」;吉本斯的詩句提到“面具/怪物戴上/餵食/捕食它們的獵物。”事情遠非一帆風順,但是,從巴羅編排的鼓樂循環中舒緩的動盪中可以看出,正是自信,就像整張專輯一樣,最終定義了她的語氣。
然而,另一種不同的動盪正在等待著樂團。就像之前的 Massive Attack 和之後的 Tricky 一樣,Portishead 在一張突破性的首張專輯後突然成名,但他的反應卻是困惑和厭惡。廣泛認可並不等於普遍理解。假的沉重的、常常令人不快的主題常常被忽略。樂團的超音速成為晚宴和電視節目的素材,這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錯。主流同質化是巴羅特別煩惱的一個根源。巴羅不滿 25 歲,來自工人階級背景,他討厭這樣一個事實:他的聲音雖然從未打算為火鍋和 BBC 第二台伴奏,但在某種程度上卻與它們兼容。吉本斯和厄特利雖然較少公開表達他們的不滿,但也有相似的觀點:吉本斯在接受採訪時完全放棄了與媒體交談。
當樂團聯合起來策劃他們的第二張專輯時,他們是在一種在最初的會議上幾乎沒有的緊張感下完成的。假的追溯了自身自由發展的敘述;這個敘述的基本隱私源於這樣一個事實:這三人對公眾來說是不可見的。在媒體曝光之後再重複它的聲音,本質上是不真誠的;這樣做只會給自己打上烙印,同意自己淪為商品。錄音過程非常艱苦,因為樂團追求一種能夠抵制和拒絕不良曝光的真實性模式。巴羅和厄特利從頭開始製作自己的樣本,錄製樂器,將它們壓到黑膠唱片上,並在最終採樣之前對唱片進行磨損。同時,吉本斯寫的歌詞中的不滿和緊張不可能被誤認為是其他任何事情。以前,他們是三個人組成一個樂團;現在,他們是一個樂團。現在,他們既是“波蒂斯黑德”,又不是“波蒂斯黑德”,而將自己呈現為衝突中的身份似乎才合適。
20年前的1997年發布,波蒂斯黑德與其前身明顯相關:樂團 2008 年第三張專輯的更明顯的背離第三以及兩張專輯中的歌曲在 1998 年現場合輯中的融合羅斯蘭紐約現場演出讓分組變得更容易假的和波蒂斯黑德一起。這些相似之處長期而深刻:碎拍和厚重的低音,深思熟慮的吉他,甚至更有深思熟慮的歌手。但比例已經改變。低音音符的流行假的創造了一種永久懸浮在液體中的感覺,就好像聽者正在穿過一顆心,但除了華麗的“Undenied”之外,波蒂斯黑德展示了不再像以前那樣提供低音的表演。這些排列更乾燥、更堅硬、更粗糙、更備用;空氣和固體是這張專輯的主導元素。吉本斯的聲音語言也同樣發生了變化:雖然她總是保持鎮靜,但她的語氣充滿了好鬥和痛苦、指責和挑釁。她的主題不那麼籠罩在詩意的難以捉摸之中;她更坦率地唱出了擔憂和煩惱。
她最關心和困擾的是西方資本主義。波蒂斯黑德開場曲「牛仔」為後續歌曲中更普遍的不確定性和拒絕宣言注入了明顯的反商業維度:其中所說的「你」是一個欺騙者和壓迫者,一個戴著面具以獵物為食的人。
你給我們講了一個欺騙的故事嗎?
隱藏那些需要說話的舌頭?
微妙的謊言和髒硬幣;
真相已售出,交易完成。
其他歌曲也以此為主題。 《半日閉幕》指的是“金錢萬能的天空日漸縮小,讓我們如痴如醉”,並宣稱“夕陽下,商人的沉默讓我們窒息”;更接近的《西方之眼》談到「不忠實的貪婪鞏固了甜蜜的慈善事業」。這裡起作用的不僅僅是脆弱的反企業言論:雖然吉本斯的聲音聽起來與查克·D 的聲音完全不同,但她同樣有興趣詢問誰偷走了靈魂。她對基督教概念和形象的投入使她將資本主義、商業宗教視為一種頹廢,一種背離慈善救贖的方式。隨著白晝和太陽(和兒子)在西方消逝,世界被利潤動機及其無情的不誠實所束縛和壓制,靈魂——或者至少是自我——陷入癱瘓,永遠疲倦和不安。錯誤的生活無法正確地過:“選擇竭盡全力”的後果是“秋天的陰影,陳舊的苦澀結局”,而愛的行為,美麗而可怕地,被簡化為“多年的挫折,並排躺著。”吉本斯非常清楚,不能僅僅從外部進行指控:她提到“我們摧毀了我能看到的一切”,“用西方的眼睛和蛇的呼吸,我們如何讓自己的良心安息”。基督教的道德敗壞以及與西方固有的白人身分給她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她既沒有擺出姿態,也沒有提供解決方案,而是上演了一個信仰與欺騙同義的世界的痛苦戲劇。
這張專輯完全有道理,但聽起來怎麼樣?有人可能會爭辯說波蒂斯黑德理論上比實務上更令人欽佩。它的創作與快速獲利和輕鬆快樂的孿生原則直接相反,是一部痛苦而嚴謹的傑作。除了《Undenied》之外,這張專輯的興奮點雖然很多,但與其令人痛苦的政治和四面楚歌的性質密不可分。厄特利在《牛仔》中的即興演奏足以鋸斷鋼鐵;巴羅在《極樂世界》中的節奏以一種令人震驚或與炸彈相鄰的緊迫性來衡量其措施;吉本斯的聲音,沒有令人安慰的伴奏,自始至終都充滿著一種令人悲傷的純粹,達到了前所未聞的痛苦高度。假的。儘管專輯之間 11 年的差距掩蓋了這一事實,但可以肯定的是波蒂斯黑德為更深感不安的語氣鋪平了道路第三(他們最好的專輯),因為它標誌著超音速的延伸假的。
正如這 11 年所表明的那樣,找到適合這種基調的作品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對於波蒂斯黑德一點一滴都不可重複假的。在樂隊能夠正確地聚在一起之前,需要長時間的分離,並且第三,一經發布,就證明了它的獨特性;明年春天,波蒂斯黑德將整整十年沒有新專輯。考慮到樂團成員的嚴格標準,完全有可能永遠不會有第四張唱片;樂團的愛好者很可能會被三首傑作所困,僅此而已。儘管它不是三者中最好的,但時間仍然證明了其創作的嚴酷性並見證了其持續的共鳴。隨著資本主義的破壞倍增,信仰變得更加唯物主義,這張專輯對貪婪、悲傷和救贖的關注只會變得更加重要。波蒂斯黑德在美國嘻哈音樂(他們最初從中汲取靈感的領域)的支持率仍然是 100%:藝術家喜歡文斯·史台普斯,崔維斯·斯科特,肯伊·維斯特, 和男生Q他們都是布里斯托三重奏的熱心崇拜者和學生。二十年過去了,但作為巴羅、厄特利和吉本斯正直及其自身必要性的證明,波蒂斯黑德仍然不向任何人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