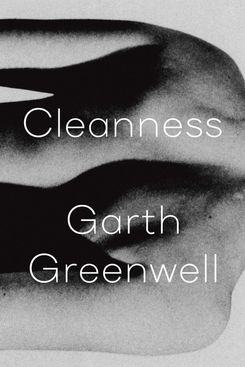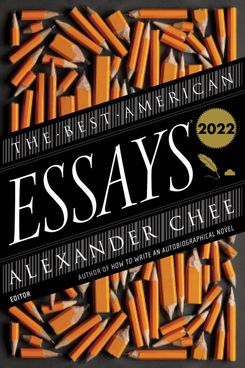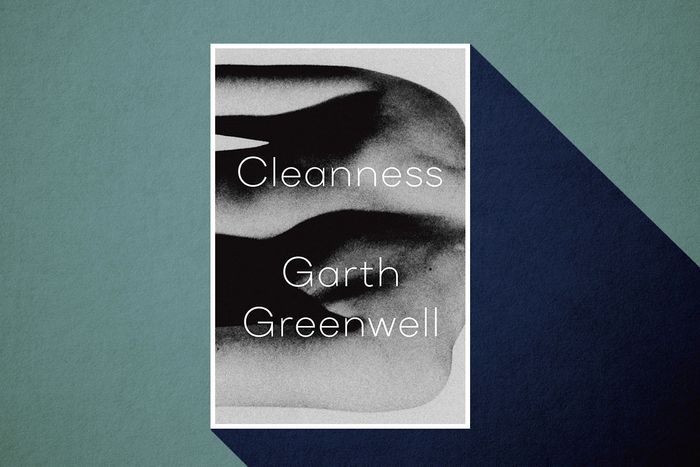
亞歷山大·奇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寫性在我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複雜角色——它是羞恥和慾望、傷害和恢復、失望和深刻的根源。儘管人們可能會試圖將他的作品分為兩個不同的陣營——文學和情色,但切相信情色在他作為文學作家的作品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文學和色情之間的鴻溝並不是任意的,但它們之間的鴻溝並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麼大。 Chee 的選擇是《青蛙王》故事的節選加斯·格林威爾2020年的小說清潔度,是文學如何運用情色寫作策略的一個令人驚嘆的例子。在這個場景中,敘述者和他的愛人正在度假,沒有受到可能不同意他們關係的朋友和家人的監督。他們是匿名的,在公車站接吻,敘述者擔心他們太明顯了——直到他意識到可見性才是關鍵。他的愛人渴望他們在其他地方無法獲得的曝光。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暴露時刻,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因為敘述者了解到他可能像他的愛人一樣喜歡觀眾。
這種自我揭露正是奇在偉大的性愛寫作以及所有寫作中所欣賞的。您可以閱讀下面的摘錄,以及 Chee 的想法。
摘自《青蛙王》:
「後來我在等開往城裡的巴士時才想起這件事。我們是車站小避難所裡唯一的人,擠在一起頂著風,風比我想像的還要猛烈。天氣不是很冷,但對於我們的外套和出門前我們互相圍著的圍巾來說已經足夠冷了。然後R.走上長凳,他抓住我的肩膀,讓我面對他。現在我長高了,他說,然後彎下腰來吻我,但不是貞潔的吻,他抓住我的頭髮,把我的頭向後仰,用舌頭探探我的嘴。我笑著試圖把車開開:那是一條繁忙的道路,過往的車輛都在我們的視野中。但他緊緊地抱住我,急切地吻著我,直到我意識到暴露才是重點,他想炫耀,在這裡沒有人認識他,在這裡他可以匿名和自由,可以實現坦率的理想。他靠向我,把他的骨盆壓在我的肚子上,讓我感覺到他的陰莖在我們之間堅硬;他竟然會這樣炫耀,我完全沒想到。我抓住了他,用我的身體來保護我們,我用雙手隔著他的牛仔褲用力地抓住了他。我開始解開他的腰帶,想要見見他的勇敢,向他表明我是個遊戲者。他在我嘴裡呻吟了一聲,然後收回手,推開了我的手。表現良好」他輕拍我的臉,笑著說,乖點。”
格林威爾在一篇文章中寫了這篇文章試著寫一些關於幸福的事——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練習。我被整個故事中對歡樂的關注所吸引。關於酷兒性的事情是,它確實是一場基於身體愉悅的革命。你的身體體驗到的事實與文化告訴你的可能或理想的東西背道而馳——所以你既被它吸引又害怕它。描寫性是描寫人們如何認識自己、如何溝通的一種方式。因為性就是溝通。因此,從很多方面來說,當你在故事中加入性時,就像加入對話或手勢一樣。它是這些東西的組合,也不僅僅是這些東西。
在這個場景中,敘述者和他的男朋友擔心被看到在公共場合接吻。但敘述者很快就會明白曝光才是重點。因此,自我揭露有多種形式──你向愛人以及世界展現自己。敘述者發現他的愛人有暴露狂的癖好,敘述者可能也會有這種癖好。正如格林威爾所說,他可能希望遇到這種大膽的人。
這個場景的寫法有一種令人震驚的特質。這一刻被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但身體也能感受到它。我真正欣賞格林威爾寫作的一件事是他對身體的關注。屍體在做什麼?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很多當代寫作都是沒有實體的。但他把我們帶入了吻的細節時刻,進入了它的中心,點燃了他自己和愛人的興奮,並將其變成了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
當吻開始時,你不知道它會去哪裡。這一刻比預計的公車站之吻要遠一些。有一種好玩的感覺。當他們在故事後期發生性關係時,它反映了這個場景,使用了相同的短語 - 但由敘述者而不是情人使用。這一次,他們可以做自己了。沒有向觀眾展示的感覺。
將性納入文學就是將全方位的經驗納入其中,就像納入歡樂一樣。關於我們如何在當代寫作中描寫創傷和痛苦已經有很多討論,這似乎是從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還是一名寫作學生時非常常見的一種對待痛苦的方法中產生的。人們認為疼痛是物質的。如果你發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得到的回應是,“好吧,恭喜你的材料。”但如果是的話太糟糕了,那麼你可能會被指控利用你的痛苦。我們很輕鬆地談論了疼痛。但沒有人告訴我如何像格林威爾那樣寫快樂。
當我首次亮相時,我是一群被認為在作品中特別大膽地包含性內容的作家中的一員,他們是酷兒作家。我的第一部小說中有大量的性內容。當時並沒有試著思考,為什麼我把它包括在內?我在做什麼?我以為我在做什麼?作為藝術家,您會思考所有這些推動和拉動您的不同問題。我想我是想寫一些性愛恢復的方法。性暴力後性可以讓你恢復身體的方式。性就像繪製自我地圖;每次你擁有它,你就會更了解如何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