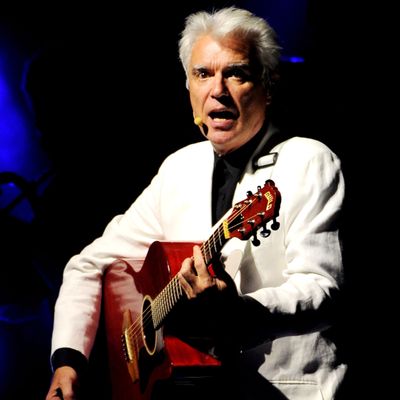
大衛伯恩 (David Byrne) 與 Talking Heads 樂團一起度過了他職業生涯的早年,用他的藝術來擁抱無意義的事物。現在他似乎對社會中什麼是良好的判斷力更感興趣。這並不是說沒有一些令人愉快的奇怪時刻美國烏托邦,他 14 年來的第一張個人錄音室專輯——還有很多——但他的音樂之外的項目越來越多地為其提供了背景。他的部落格內容涵蓋所有內容王牌到槍枝管制已經將他的個人色彩釘在了桅杆上,現在有他的系列講座兼網站,快樂的理由,其中他收集了正在嘗試激進的社會政治舉措並取得巨大成功的城市和社區的實例。例如,當溫哥華決定將毒癮視為健康問題,而不是犯罪,它導致了服藥過量的減少和犯罪率的降低。正如他在講座中指出的那樣,“一切都是相互聯繫的。”
記錄中有很多關於金錢的提及,強調了金錢塑造我們生活的問題方式。
哇,太棒了。我意識到,是的,我把這些參考資料放在那裡,但幾乎沒有其他人注意到這一點。我寫作時並不是帶著這樣的意圖,我不會寫出「我不得不說一些關於經濟學的事情」之類的東西。但它出來了。通常,當你寫完一些東西後,你會意識到,「哦,這就是它的意思。這才是這裡真正要說的。
你對錢的感覺如何?你能想像一個沒有它的系統嗎?
我可能已經打電話記錄了美國烏托邦,但我不會提出一個沒有錢或沒有具體細節的烏托邦,例如“好吧,我們將擺脫所有的錢,我們將與任何我們想睡的人發生性關係。”不,我不會處理這些細節。但我幾個月前讀過一本書,名叫道德經濟,作家[塞繆爾·鮑爾斯]指出的一件事是,人們會自願為社區提供幫助,但如果你付錢給他們,他們就不會。當金錢進入方程式時,他們會覺得自己並不是出於自願而付出的;他們正在被收購。我用最糟糕的方式解釋了這一點,但[他所說的]是人們有時有良好的本能,但金錢有時會排擠他們更好的本能。這並不是說它沒有用,但我們可能想知道它何時會排斥我們一些更好、更慷慨、更利他的行為。
這讓我想起了《汽油和髒床單》中的歌詞:“我將從舞台上下來/市場和購物中心/進入房子——戰爭的房間/現在看著我並回憶起來。”
這就是我說的,我要來面對你們。我將進入董事會,或者是你做出此類決定的地方。你小心點!在某些時候你會遇到。
我真的很喜歡在 YouTube 頻道上舉辦講座的理由,這是一種對抗。哪個先出現-專輯還是系列講座?
大約在同一時間。沒有明顯的聯繫。有時,直到接近終點時,您才會意識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你快完成了,然後你意識到,“啊!”你會得到對它的看法。不管怎樣,幾年前,在川普先生當選之前,我和許多其他人一樣,每天讀新聞都感到憤怒和絕望。出於本能,我開始保存那些對我來說似乎有點幫助的東西。我為自己制定了規則——為了真正帶給我希望,它們必須是被證明是成功的事情。不僅僅是“有人有一個好主意”,這個想法必須被付諸實施並嘗試過。我開始收集越來越多的東西,我意識到我應該談論它。也許其他人想聽聽我偶然發現的這些事情,因為他們可能同樣感到沮喪和憤怒。這並不是說這會讓他們完全高興起來,但也許會有一點點。
我大約在同一時間寫這些歌曲。 [沒有]明顯的聯繫,但後來我開始意識到這些歌曲是對整個情況的一種宏觀看法,而《快樂的理由》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做出了回應。這並不是說一切都會好起來,而是說:「還不要放棄。這裡有一些希望的小花絮。
「Cheerful」是一個非常古雅的英文單字——講座的標題就是以伊恩·杜里的歌曲——而且它還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暗示著被動性。然而,這次講座似乎不是為了讓人們感覺良好,而是為了鼓勵他們了解自己實現改變的能力。
是的,不用我說“滾開,做點事情”,人們就會感覺到這些都是正在發生的真實的事情,人們正在做的真實的事情。儘管我非常喜歡[杜里]的歌曲,但這不僅僅是享受一杯茶和一杯雪糕的樂趣。這是指人們正在做的事情,不需要觀眾採取行動,但他們說,“這些人已經做了事情,這些人正在做事情,這並非不可能。”
是什麼讓您覺得有責任傳播這些知識?
我開始認為,身為公民——身為世界公民,無論如何——我們有義務比以往更積極參與。我們有點袖手旁觀,感覺就像,“哦,我可以每隔幾年投票一次,這就是我所做的。”我認為現在的感覺是,“也許我們需要做的不止於此。”也許為了保持我們的希望和民主完好無損,也許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每隔幾年拉動槓桿。
這對我來說很容易說。我是一名成功的流行音樂家,我不能對人們說:“做我所做的事。”不是每個人都能做我所做的事情。但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參與方式。
在講座的問答環節,有人問“我如何融入社區?”我喜歡你說參與必須來自讓你感覺良好的地方,而不是來自內疚或羞恥的地方。
是的,那不會很有趣。
你是否曾經處理過內疚感或羞恥感?如今,人們對白人特權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有了更廣泛的理解。但也存在著“白人內疚”,這往往會導致表演性行為,而不是真正的改變。您對此有何看法?
情況很複雜。我必須說我可能不會感到內疚,但我也覺得為了做正確的事,需要不斷的認識和奮鬥。有必要。
「Doing the Right Thing」這首歌感覺就像是對特權的串燒。
是的,這有點串燒。大多數歌曲都不是。這有點諷刺。你的旋律非常優美,但卻有些尖刻。很多詞先於音樂。並沒有完全將它們塑造成所有的詩句和副歌,但在音樂進來之前已經做了很多準備。 [笑。
您是如何召集唱片中的年輕合作者的?
一個名叫 Mattis With 的人,是一家名為 Young Turks 的小廠牌的合夥人,[幫助了我。我[一開始]沒有提到這張唱片。然後有一次我說:「你知道,馬蒂斯,我一直在製作一張唱片。你想聽聽嗎?我為他演奏了它,他真的很喜歡它,但他說,“我認為你可以更進一步,我想我想推薦其他一些人作為合作者和貢獻者。”所以他在這方面確實很有幫助。我已經認識一些人,像是 Sampha 和 Dev Hynes,他們玩過一些東西——我們以前一起做過東西。但還有很多其他的,我不知道——OPN [Oneohtrix Point Never],我不知道。他進來了,我們相處得很好,所以當他說,“我有一些曲目,也許你想看看你是否可以做點什麼,”我說,“當然,當然。”
每一代的藝術家都必須嘗試弄清楚他們的音樂語言是什麼,以及他們想要回收或拒絕多少過去的語言。這種探索在專輯中非常明顯。還有鄉村音樂、環境音樂和流行音樂等等。這些並置仍然像你剛開始時那樣讓你興奮嗎?
是的!我感覺很多音樂家正在以一種與我想像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他們帶來的聲音和音樂理念。這太棒了。
有何不同?
一首歌中有一個部分——我忘了是誰唱的——聽起來完全混亂,就像節奏完全斷裂一樣,但效果很好。只要我能在一切都在崩潰和崩潰的情況下保持歌唱的順利,那麼一切都會再次恢復正常。這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這就是為什麼你邀請人們[合作]。
在“每個人都來我家”中,有一個部分——“我們這輩子只是遊客”部分——完全消失並進入中場休息。它不是來自我。我的演示仍在進行中。這是合作者帶來的另一件事。
你之前製作過的專輯大部分都是女性,但我注意到了美國烏托邦都是男人嗎?
是的,我想是的。這不是故意的。 [註:本次訪談結束後,大衛伯恩發布了一份聲明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
本著「一切都是相連的」的精神,你對有毒的男性氣質有何看法?
顯然我們現在可以做很多事情,但這也是一個深層的問題。可以追溯到大約2000年前,當時父權宗教推翻了母權宗教,或者說擁有多個男女神的宗教。好吧,那是從哪裡來的?這是因為城邦和農業的崛起以及這種行政控制的需求嗎?我沒有答案,但那裡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儘管人們可能認為[父權制]是我們本性所固有的,但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兩千多年才剛過去,誰知道未來會怎麼樣呢?可能會發生不同的事情。
我讀了《聖經》中的《創世記》的漫畫版。它逐字逐句地遵循它。你意識到這是一個充滿了毆打和掠奪土地的骯髒故事。討厭的東西。 [作者 R. Crumb] 逐字逐句地寫了這本書,並在後面寫了自己的評論。很多內容都是這樣的:「等一下,這個角色,你現在回頭看,原來是個女人。他們把它從女人變成了男人,但他們忘記修正故事的一些方面。在一些書中,故事中存在著這種奇怪的脫節,一些敘事上的小問題不太有意義,因為他們改變了某些人的性別。就像,嗯,好吧。[笑.]
宗教有助於建立父權制。
是的,宗教說:「這就是上帝所希望的樣子」——最終的理由。
在班輪註解中美國烏托邦您強調,殖民美洲的歐洲人相信他們正在實現烏托邦,但他們卻要為土著人民的種族滅絕和非洲人民的奴役負責。歷史對烏托邦的定義常常建立在對他人的征服之上。我們可以如何找到通往烏托邦的不同途徑?
我的回應是環顧世界,看看是否能找到一個地方,他們以更公平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並且似乎取得了成功。我不知道那可能在哪裡,但我想它可能是一個小社區,也可能是整個國家。開始尋找:他們在做什麼?對他們來說效果如何?
釋放美國烏托邦大約在同一時間,《快樂的理由》感覺很聰明,因為,就像你說的,它們互相指向。這張專輯可以幫助擴大系列講座中提出的對話。
在某種程度上,是的。這給了我除了寫歌之外的其他話題,有時這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我們也談談其他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