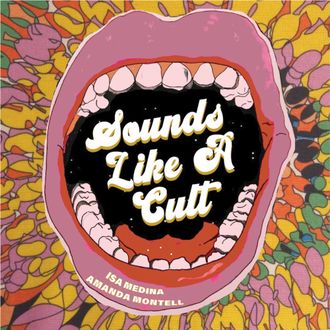
這幾天空氣中瀰漫著濃濃的崇拜氣氛。它似乎無所不在。這裡有川普主義、卡農主義和其他有極端主義傾向的著名政治意識形態。但除了明顯嚴肅的材料之外,它還存在於文化中:存在於我關注的 YouTube 和 TikTok 明星中,存在於他們眼中的閃爍以及他們培養的以人格為驅動的追隨者中。它甚至出現在我訂閱的子堆疊中,其中一些本身就是緊密的、受意識形態限制的團體。然後是我最近看的電視:我們墜毀了,以傑瑞德雷托 (Jared Leto) 對亞當諾伊曼 (Adam Neumann) 偽耶穌能量的印象為特色;遣散費,其主題強調企業宗教信仰;在天堂的旗幟下,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我住在愛達荷州也沒有幫助。
但我並不是唯一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人——這些感受被隱藏在偉大的聽起來像是邪教,All Things Comedy 發布的新播客。被描述為“喜劇邪教播客”,每一集都採用文化中的不同現象,並使用一定的特徵框架來確定其“邪教”程度。每期都以一個問題結束:這個次文化是「過你的生活」邪教、「小心你的背後」邪教,還是「滾蛋」邪教?過去的主題包括LuLaRoe、Tony Robbins 等明顯的目標,以及多層次的營銷計劃,但當展開更多意想不到的主題時,該節目最有趣:有毒的關係(“對一個人的崇拜”)、學術界,以及,呃,腳。這 結果 是一個非常有趣但輕鬆的話題,它通常是一個沉重的主題,在播客的輕鬆和輕微的荒謬中,它觸及了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無論你身在何處,你永遠不會離崩潰的邊緣太遠。
該節目由作家阿曼達·蒙特爾和紀錄片製片人兼單口喜劇演員伊莎貝拉·梅迪納主持。前者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崇拜:狂熱的語言,它探討了語言如何成為培養類似邪教動力的核心,以及對語言的操縱如何滲透到我們文化中看似平凡的領域(例如企業界)中複製這些動力。
當我們三個人最近交談時,蒙特爾談到播客在技術上是她書的延伸,源於她弄清楚如何處理她分析的許多被排除在最終草案之外的群體。加入蒙特爾的計畫後,梅迪納帶來了製作敏銳度,以及對邪教更加好奇的敏感度。 “我們問自己,我們如何為這些東西做出實際的有成效的貢獻?我與他們談論了他們自己與主題的關係、現代社會中邪教動態的共鳴,以及他們用來評估「邪教」的方法。
邪教似乎通常是文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但是什麼特別吸引你們倆把它們作為主題呢?
蒙特爾:嗯,我是和一個邪教倖存者一起長大的。我父親在一個臭名昭著的邪教組織中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期西納農。它最終並沒有像瓊斯鎮和天堂之門那樣出名,因為沒有發生大規模自殺或兇殺事件,值得慶幸的是,但它是一個控制非常嚴格的組織,總部位於灣區的一個偏遠公社。它的鼎盛時期是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最初是一個替代性戒毒中心,後來發展壯大,以容納那些想要加入那個時代蓬勃發展的反文化運動的人。我父親的父親——一位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者和偽知識分子——想要參與這個實驗,所以他和我父親一起搬到了這個院子裡。我父親立即非常懷疑。
我是聽著儀式、服從以及在那裡發生的一切的故事長大的。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注意到邪教對各種文化的影響:新創文化、SoulCycle、戲劇節目。 (我們剛剛拍了一集論對戲劇小孩的崇拜.)對於我的書,我從語言角度進行了探索,因為我在大學學習了語言學和創意寫作,這對我來說是最自然的方式。
麥地那:對我來說,更多的是讓我覺得我是那種嘗試每一種「邪教」的人。我在大學時參加過聯誼會。我會站起來。我們做到了我們在 SoulCycle 上的試播集在疫情期間,我每週都會去參加戶外 SoulCycle 課程。
我認為這是因為我感覺自己從來沒有真正融入任何地方。我是拉丁裔,我是同性戀,我是雙性戀,我是移民。就是那個第三文化小孩事物。所以世界之間總是有一種平衡感。我也不喜歡被束縛,所以我喜歡嘗試一切。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傾向於提出這樣一種觀點:“好吧,情況並沒有那麼糟糕”,而阿曼達則在分析它,並且更多的是,“你應該小心你的背後。”
我見過聽起來像是邪教最近出現在很多不同的圈子裡,所以我的印像是這個節目引起了人們的共鳴。您認為您的聽眾會被什麼吸引?
麥地那:部分原因可能只是時代。我們已經走出了一個坦白說相當黑暗的時期:這是一場流行病,人們正在掙扎。邪教可能非常黑暗,所以對於那些只想在上下班途中聽點東西而不是深入了解新聞的人來說,以輕鬆的方式對待嚴肅的事情的想法會讓他們感到耳目一新。
蒙特爾:我認為我們文化中的崇拜意識也確實在飆升。邪教往往在社會政治動盪時期蓬勃發展,對嗎?這就是我們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所看到的,當時民權運動、越戰和甘迺迪遇刺讓人們感到存在的失落。人們對那些本應提供社區感、聯繫感和身份感的系統失去了信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那個時代看到瞭如此多的團體的出現,從山達基到猶太人的耶穌。我們現在正處於相似的時期,大流行無疑使我們遠離了傳統的社區和儀式來源。因此,人們開始轉向這些另類的、經常在線的邪教社區來填補空白。我想我們都注意到了這一點。
正如艾薩所說,用世界末日的語氣談論這些事情很容易,但這不是我們是誰。儘管我們持懷疑態度,但我們從根本上也持樂觀態度。有時人們只是想讓我們純粹地對本週所談論的事情進行拉屎,但這與我們思考事物的方式是相反的。
麥地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每一集的結尾都有這些類別:「過你的生活」、「小心你的背後」或「滾蛋」。我們經常最終坐在不同類別之間,並且我們提醒聽眾,這些只是我們的觀點。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感受。
蒙特爾:而且,邪教的定義非常主觀。它充滿了判斷力。我在本書中訪談過的每一位學者對於區分邪教與宗教或其他受意識形態束縛的團體的標準都略有不同。承認這種主觀性很重要。
好吧,讓我們談談這個,因為該劇的節奏主要涉及通過弄清楚他們與邪教動態的接近程度來運行各種時代精神團體。您如何描述您使用的框架?
蒙特爾:是的,這就是我們開始製作這個節目時面臨的挑戰。一切都可以是邪教,那麼我們如何對其進行更明確、更細緻的定義呢?起初,我們列出了九種不同的品質,如果其中兩三個被勾選,那麼它就是「小心你的背後」。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場,那就更像是一種「過你的生活」的現象。但就是感覺這樣太麻煩了。這不應該成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用來判斷某物是否具有危險文化的正式分類系統,但我們認為這是開始對話的好方法。
儘管如此,我們的腦海裡仍然有一個標題。是否存在「我們與他們」的心態? 「目的證明手段合理」的哲學?是否有一位具有統一魅力的領導者?有超自然的信仰嗎?我們在談論金融剝削嗎?最壞的情況是什麼?
麥地那:有時我們對某些特定主題的崇拜程度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們通常全心全意地同意「滾蛋」的東西。
蒙特爾:這很大程度上與不受控制的權力有關。我們即將推出關於伊隆馬斯克的一集,我們對他有很多……看法。但在評估一個群體時,直覺並不總是足夠的。我們帶著自己的偏見而來。在談論這個主題時,一些麻煩在於「邪教」和「洗腦」這兩個詞被隨意地亂扔——尤其是現在,意識形態分歧如此之大,每個人都互相看著對方,想著對方一個人在邪教中。因此,我們想引起人們的注意,即人們對這些東西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受控制的權力濫用?這是第一號危險訊號。
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製造一種譁眾取寵或危言聳聽的感覺。更重要的是,崇拜是出現在你可能不會想到的地方的東西。像 NXIVM 這樣的團體的成員很容易被非人化——將他們視為被洗腦的傻瓜——但他們並不像人類那麼不正常。我們的播客可能聽起來像是一個關於邪教的節目,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關於人類行為的節目,以及我們如何在資訊過載和意識形態分裂的時代找到歸屬感的節目。
我仍在思考您之前關於邪教在動盪時期變得更加突出的評論。這對我來說是正確的,但我也很有趣地思考,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巔峰創業文化/技術創始人崇拜文化是如何在奧巴馬時代真正起飛的,那並不完全是一個動蕩的時期。
蒙特爾:事情是這樣的:人們往往相信的關於邪教追隨者的另一個神話是,他們真的很絕望。但在我的書中與邪教倖存者交談時,我發現共同點實際上是太多的理想主義。這個想法是可以找到世界上最緊迫問題的解決方案,透過與這家公司或這位執行長合作,你可以成為這項變革的一部分。
所以這對歐巴馬時代來說是有道理的。當然,我們的文化正在變得更加世俗。我們正在遠離我們賴以成長的有組織的宗教。但我們並沒有變得不那麼精神化或對社區的關注。現在更多了,好吧,我不會每個星期天都去教堂,但現在我的創業就是教會。
麥地那:你也許還可以補充一個事實,即奧巴馬時代的全部內容是:「我們將改變一切。我們將共同改變世界。
在我看來,數位媒體生活的許多內容——建立追隨者、「準社會性」、成為「影響者」、財務關係等等——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映射了邪教的某些動態。你的播客本身會是一個邪教嗎?
麥地那:[笑了。】 這是有可能的。前幾天我們在播客上開了這個玩笑。我們當時想,“誰會心甘情願地跟隨某人並為他們的友誼付出代價?”
蒙特爾:我認為,如果我們開始說我們不是邪教領袖,那麼我們很可能就是一個邪教。 [笑了。] 是的,不,這又可以追溯到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過載的時代。我們中的許多人感到壓力很大,需要對陽光下的每個話題進行簡潔、自信、消息靈通的論證,所以我們當然會默認那些在公共場合自信地談論任何事情的人。就像那個獨白跳蚤袋:“我希望有人告訴我早上要穿什麼。”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我確實在思考那個場景。
蒙特爾:就是這樣吧?這是選擇者悖論。當你覺得可以在其中看到自己的人告訴你「事情就是這樣」時,你很容易就會同意。但我們不斷強調這只是我們的觀點。
麥地那:此外,如果我們是一個邪教——我們是邪教領袖——我們仍然是閱讀評論並對聽眾做出回應的邪教領袖。我們徵求他們對要做什麼劇集的建議,並包括他們的電話。我們和聽眾之間是透明的。所以我想這讓我們成為了「活出你的生活」的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