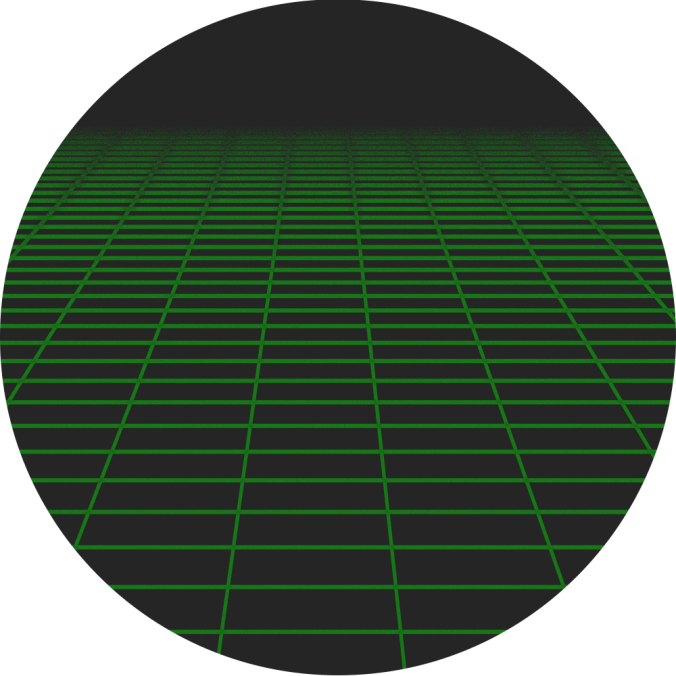
瘋子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有爭議的節目——看看我們之間的差距就知道了預播狂歡以及我們的更多無聲的情節回顧——部分原因是劇集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當最後的片尾字幕滾動時,你可以為這部劇的命運多舛的主角描繪出清晰的敘事弧線,但它們的講述風格卻非常模糊,從一個近未來的反烏托邦喜劇開始,然後深入到回憶的情景幻覺中。撫養亞利桑那州,東方的承諾, 和魔戒等。對於每一個新的遠景,導演卡里·福永 (Cary Joji Fukunaga) 都會轉變為一種全新的風格,在必要時採用水平擦拭和令人難堪的暴力以及單次動作鏡頭。
但其中最充分實現的是頂層現實世界,一個替代現實,正如福永和創作者/作家帕特里克·薩默維爾所描述的那樣,與我們的相同,直到「90 年代發生了一些事情」。一些流行文化發展迅速:有提到馬達加斯加,採取,老百姓,以及長時間的《警察》封面(被史汀現實生活中的妻子特魯迪·斯泰勒迷倒在銀幕上)。視線中沒有手機;科技似乎還停留在 80 年代初期的陰極射線放克時代,顯示器上發出厚重的 Atari 風格的圖形。網路就在那裡,但是是模擬的,有名為「Dox Stops」的實體店可以滿足您所有的身分駭客需求。在紐約北灣,矗立著一座桑德斯式的額外自由女神像,看起來就像某種揮舞權杖的愛國主義劊子手。薩默維爾將這種增強版的現實描述為賦予該劇「一些喜劇能量和一些喜劇可能性」的一種手段,而這種手段不會基於角色的心理健康狀況——這個問題困擾著原版的挪威版展示。在夢境世界中,喬納希爾(飾演歐文)和艾瑪史東(飾演安妮)展現了他們的喜劇才華,但在現實世界中,幽默來自社會本身——特別是來自這部劇對我們的社會的黑暗可信的推論。
長期以來,這個術語一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某種進化步驟,是 Uber、Airbnb、Fiverr 等公司所設想的未來,每個人都可以在需要的時候自由地工作。事實證明,這些無休無止的零碎工作並不能真正提供穩定或有回報的就業感,更不用說醫療保健甚至很多錢了。當應用程式指示你工作時,你的工作最終會比當值班主管給你發短信時工作同樣不人性化,甚至更不人性化。瘋子讓這種趨勢變得更加激烈,想像一下在紐約,每個人都賣掉所有東西只是為了買得起鞋盒公寓。這個笑話很早就以 Ad Buddies 的形式出現,這是一種信用系統,允許人們透過真人追蹤他們、大聲朗讀廣告文案來支付商品和服務的費用——這是彈出式廣告的終極形式。希爾在爸爸之家尋找一份工作,這家公司讓男性扮演剛過世的父親的角色,直到他發現自己必須這麼做支付以獲得從事這項工作的機會。受僱的演員獲得人事檔案作為付費好友代理人,結果往往令人沮喪。這個笑話既是關於這些工作的存在,也是關於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們的痛苦。高維護成本本·辛克萊 (Ben Sinclair) 一度打破了朋友代理人的角色,沉思道:“我討厭我他媽的生活。”
儘管生產設計令人瞠目結舌,但相同的零件她和外星人,這種晚期資本主義的地獄景象讓人感覺異常可信。事實上,我們已經差不多做到了。最近的兩篇文章大西洋報和紐約客探討了以下現象家庭浪漫是一家日本公司,僱用了大約 800 多名演員,為日益孤立和孤獨的人群充當父母、孩子、老闆、朋友和情人。其中一些故事令人震驚:一個小女孩在成長過程中相信一名演員是她的父親,以及他因向她隱瞞真相而痛苦;整個婚禮都是由表演者安排的,只是為了滿足父母的突發奇想;訂單表格詳細說明了服裝選擇和個性偏好,然後一次持續多年。瘋子將這一點映射到美國,設想一個人類像我們一樣願意出賣自己身分的世界,儘管是透過更具體的手段。當我們用我們點擊的每一個「在 Facebook 上登入」小部件來交換隱私以換取便利時,靈魂骯髒的居民瘋子紐約將他們的身份和個人拍賣給出價最高的公司。 「人格」和「職業」交織在一起,一起螺旋式下降。
對於這部劇的很大一部分——你可能會說,這部劇的更好的一半,這取決於你願意在多大程度上追隨它的幻想線索直到最後——它似乎被職業和身份之間的緊張關係所主導。歐文拒絕他的家族企業在最低層作為無人機工作,避開他們的豪宅,住在羅斯福島的膠囊裡。在鎮上多次看到安妮的廣告後,他開始迷戀安妮——但是,她承認,這僅僅是因為她「把臉賣給了一家股票圖片公司」。對她來說最大的創傷是她姐姐的死亡,因為一名疲憊不堪的拖車司機駕駛了 30 個小時,將她們開出了公路。歐文最大的創傷是迷戀一位朋友代理,他太相信這個虛假的現實,以至於永遠把她嚇跑了。保全人員不斷地與真正的警察進行比較,捍衛他們漫無目的的權威。你最終會想到,整個喜劇發生在一個工作場所:一場迷幻的臨床試驗,參加者是零工經濟拾荒者,他們願意用自己的心理健康來換取一大筆現金。最終,該劇最大的批評不是藥物或臨床治療,而是曼特雷博士(賈斯汀·塞洛克斯飾)和他的媽媽(莎莉·菲爾德飾)的超級資本主義和野心主義表現。
希爾和史東非常適合這種後身份環境,消失在帶有狂躁喜劇能量的華麗口音和服裝中。這產生了該劇中一些最好的笑話——斯通不情願地忍受著精靈般的幻想胡言亂語,希爾在一場奇異的間諜活動中充滿了奇愛——以及一些最感人的時刻,例如當他們在幻想中打破角色並短暫地融入他們的真實世界時。透過這種方式,該劇的幻覺情節成為了表演本身的代表,讓演員(和福永)能夠突顯他們選擇一生居住的虛構世界的荒謬性。當歐文和安妮回到現實世界時,他們並沒有動搖他們在幻想中的生活;他們敏銳地記得他們的夢想孩子以及他們在模擬中分享的非常真實的情感聯繫。他們似乎在說,當你推銷自己時,你永遠不會下班。這對於一個Fiverr“實干家”因為它是個人品牌小販或主要演員。看內陸帝國為證明。
這是樂趣的很大一部分瘋子:找到一條線並拉動,直到彈出大衛·林奇或“內心之光”或今敏或菲利普·K·迪克。科幻小說最擅長的事情之一就是將廣泛、抽象的想法轉化為具體、幾乎可導航的空間。你知道瘋子紐約是因為它看起來和聽起來都很像我們所知道的紐約,但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可識別的精神空間,一個無盡的喧囂和一杯咖啡的空間。這是令人疲憊和悲傷的,幸運的是,也很有趣。但它在這樣的想法中找到了一些希望:在這個充滿影響、模擬、即興表演和演出的密集漩渦中的某個地方,兩個人之間可以建立真正的聯繫。這部劇最終感覺像是對這一事實的慶祝,也似乎是對現實世界的反駁,正是現實世界讓安妮和歐文首先變得如此荒涼和受壓迫。這一切都以逃離現實、逃離這座城市、建造它的力量而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