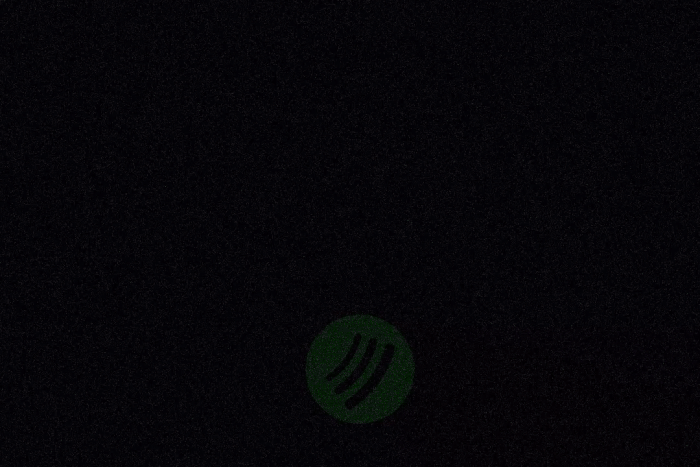
作為面向消費者的產品,Spotify 多年來一直表現不佳。無論這個平台在早期有多麼功利主義的優雅,現在都已經讓位給令人困惑、醜陋的演算法斑點,其中包括影片、播客和有聲讀物,當你在尋找自己喜歡的音樂時,你並不想要這些。當我寫這篇文章時,我的「主頁」標籤上正在播放一段關於人工智慧的自動播放技術兄弟剪輯,Spotify 決定將其推到我面前,因為它是「趨勢」。這清楚地表明這家瑞典公司正處於作家科里·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所說的技術平台週期之中“實體化」。具體來說,在獲得了龐大的用戶基礎並面臨實際賺錢的壓力後,Spotify不再擔心自己的質量,而是盡可能地從用戶的骨頭中吸取骨髓。
但蠕蟲終於轉動了嗎?儘管 Spotify 仍然是音樂串流媒體領域的巨頭,擁有 6.26 億用戶,但上個月的 Wrapped(通常是該公司的營銷利好)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低調。使用者表示鋒利的 失望由於缺乏數據特異性,他們習慣回顧過去。有些人觀察到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使用似乎很草率,在 Spotify 持續不斷的背景下,這看起來更糟。裁員。同時,一些著名的音樂家,包括 RAYE 和 Amy Allen,已經宣布他們不會參加該公司的格萊美年度歌曲作者派對,以抗議該串流媒體微薄的版稅費率。此前,美國國家音樂出版商協會就 Spotify 的行為向聯邦貿易委員會提出投訴。使用其成員的歌詞他們聲稱這侵犯了播客和混音功能,並在新的訂閱計劃中將音樂與有聲讀物捆綁在一起,他們認為這將進一步壓低版稅。
所有這些都是說,莉茲佩利 (Liz Pelly) 的發行Mood Machine:Spotify 的崛起和完美播放清單的成本時機正好。我非常想要一本這樣的書。佩利 (Pelly) 是一位資深音樂記者,早年以清醒的懷疑態度對待 Spotify。在這裡,她從對Spotify 前員工和來自音樂生態系統不同角落的演員的一百多次採訪中汲取靈感,創作出一部作品,透過公司崛起的視角,展示了它幫助開創的串流媒體世界對世界的影響。關於 Spotify 崛起的文章有很多,包括 2019 年的Spotify 拆解和 2021 年Spotify 播放,佩利都引用了這兩點。但心情機《Spotify》是一本關於我們如何看待Spotify 作為一種現象的權威書籍,這並不一定是因為她的報道是最全面的報道,而是因為佩利持續地審視了該公司如何影響並繼續影響著這個世界。
佩利的最終形像是世界末日。在圍繞 Spotify 的音樂生態持續萎縮的時代,它力爭成為一個全面消費的平台,這意味著參與式音樂文化完全崩潰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取而代之的是音樂只是填充物的平行世界。 「流行音樂、增強情緒的背景音樂和獨立藝術創作的業務應該生活在同一個平台上,在相同的經濟安排和相同的參與工具下,這一建議是一切都被扁平化的秘訣進入一股不間斷的放鬆溪流,」她寫道。 Pelly 最引人注目的貢獻是她對Spotify 的激勵結構似乎正在推動我們走向何方的觀察:走向某種賽博朋克文化的未來,該平台將音樂完全重新語境化為被動情緒調節的手段,正如Pelly 所闡述的那樣,這幾乎就是人們對它的看法音樂多年。不難看出人工智慧的崛起如何讓這一切變得更糟。另外 ”幽靈藝術家該公司被指控部署將播放清單與庫存音樂打包在一起,並進一步降低版稅率,Spotify 已經充斥著由平台遊戲演員製作的白噪音流,這些串流媒體將實際音樂排除在外;想像一下,當該技術允許他們進一步擴大努力時會發生什麼。
當然,Spotify 並不是音樂生態惡化的唯一罪魁禍首。可以肯定的是,你可能會陷入一個深深的兔子洞,周圍的串流音樂產業遠非一個好的行業。關於商業廣播和唱片公司的企業合併如何維護一個極其不公平的體系的故事不勝枚舉。但Spotify是負責在商業模式中開闢自己的主導地位,該模式進一步將音樂的生產和消費貶值到原子規模。佩利引用了音樂家兼作家達蒙·克魯科斯基(Damon Krukowski) 的話,他為Pitchfork 撰寫了一篇關於串流媒體時代藝術家版稅的定期專欄:「當我開始製作唱片時,經濟交換的模式非常簡單:製作一些東西,定價高於其成本如果可以的話,製造並出售它。現在這個模型似乎更接近金融投機。同樣不同的是,Spotify 如何完全抓住了那些現有的企業參與者,為一個稍微新的系統服務,該系統加深並加劇了舊系統的蹩腳,同樣的首要問題是少數獲勝者足夠強大,足以定下基調並不真正想要任何其他東西。當然,Spotify 有其競爭對手,例如 Apple Music 和 Tidal,但它們並不是真正的替代品,只是同一問題的較少表達。
2011 年,Spotify 執行長 Daniel Ek(左)與 Napster 聯合創辦人 Sean Parker。照片:Kevin Mazur/WireImage
這曾經是一筆划算的交易嗎?當然,科技平台的可供性使得藝術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受到關注。但靠每件藝術品謀生從未如此困難。雖然 Spotify 可能會讓我接觸到幾乎所有我能想到的歌曲,但過多的體驗往往會產生孤立效應。我們也正在失去其他東西,例如作品始終存在於其自身背景中的感覺。我不是你所謂的音樂人——我的傳記與篩選唱片行無關——但音樂對我的生活仍然很重要。換句話說,我和大多數人一樣是這種藝術形式的粉絲,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我對任何音樂教育的主要接觸都是在包含簡短描述的小盒子中,經過審查以符合Spotify 對企業友好的態度,這當我點擊播放歌曲時,它們被推到應用程式狹小的空間中的某個地方。缺乏充滿活力的音樂文化,面對網路谷歌變得越來越不可靠在為您提供可靠的獨立資訊時,這些框架越來越成為預設的知識點。這是一件可怕的事。 「在這個時代,我們無法就一般歷史的基本事實達成一致,然後我們賦予企業權力,創造他們自己的文化版本,從而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版本,」音樂家塔賈·奇克斯(Taja Cheeks)說。
Spotify 不斷增長的擴張野心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在逐利結構的推動下,該公司不斷尋找新的征服領域,過去幾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嘗試實現供應鏈多元化。我寫的是關於播客世界的文章,它最近的歷史中有很大一部分講述了 Spotify 入侵的故事,因為它致力於成為所有音頻產品的一站式商店。最近,它甚至開始嘗試跨界進入數位影片領域,渴望追逐 YouTube 主導的廣告收入。所有這些陰謀都是為了他們必須追求的核心指標,也就是在平台上花費的時間。佩利引用了一位前員工的話說,他回憶起首席執行官丹尼爾·埃克(Daniel Ek)的沉思,公司“唯一的競爭對手就是沉默”,這說明了Spotify 將其視為進入消費者生活的入口的狂妄廣闊的領域。該聲明反映了Spotify 的整體野心,呼應了Netflix 執行長 Ted Sarandos 在2017 年發表的類似言論,向投資者增強了該平台的潛力:「當你觀看Netflix 的當節目並沉迷其中時,你就會熬夜,”他說。 “我們正在與睡眠競爭,但處於邊緣狀態。”這種呼應是有道理的,因為 Spotify 和 Netflix 是科技平台如何成功佔領我們整個生活的具體表現。
那麼,我們要怎麼擺脫這個地獄呢?佩利促使我們思考,不要把希望寄託在一些新的技術創新或新創企業上,以「修復」音樂串流媒體,更不用說音樂產業了,因為正是商業、政治和文化的更大系統引導我們走向了一個新的領域。 「我們不能只考慮改變音樂或改變音樂技術,」她寫道。 「這還不夠。我們需要思考我們想要生活的世界,以及音樂在哪裡適合這個願景。從本質上講,她是在主張革命,而她很興奮心情機最後一章提供了各種例子,說明世界各地的人們如何試圖透過直接的在地化計畫播下這場革命的種子,例如充當檔案館的公共圖書館和成立音樂合作社。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音符,但考慮到結構性問題的規模巨大,不可避免地會讓人感覺太渺小,甚至可能很珍貴。但你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無論如何,她強調的項目都有一條主線:它們都強調遠離螢幕,轉而參與現實世界的社區和空間。也許這就是答案最清晰的表述。為了擺脫這個數字地獄,你可能真的應該離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