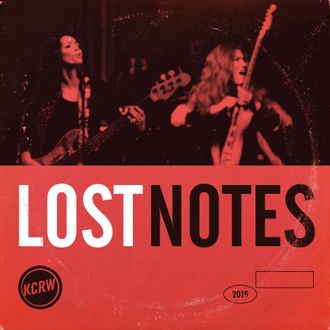
當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獲得值得多生的音樂時,了解其中蘊含的故事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我對音樂串流平台世界之前的情況並沒有特別懷念,但我不能否認,隨著時間和空間被扁平化為微小的、按演算法排序的條形,某些東西——歷史知識、文化、道德過程——已經遺失了。奇怪的是,我們感覺好像我們正在經歷某種無限的現在,而犧牲了鮮活的過去。
那種失落感油然而生遺失的筆記,KCRW 的音頻紀錄片系列提供“從未講述過的最偉大的音樂故事”,其分量隨著每一集的流逝而加深。播客最近結束精彩的第二季,該節目由芝加哥資深記者兼評論家傑西卡霍珀 (Jessica Hopper) 擔任執行製片,她從早期就開始報道音樂。雖然她現在主要是作為作家和紀錄片製片人,遺失的筆記標誌著霍珀重返電台,他多年來一直擔任音樂顧問和《This American Life》的撰稿人。
在最近一季中,霍珀收集了一個八層樓的系列,其定義是生動的道德平衡感。每個故事都將其主題視為其時代的特定產物,保留尖銳的譴責,但不一定會讓他們擺脫困境。我們追求的不是判斷力的分配,而是對複雜性的深刻認知。
正在播放的故事包括:龐克樂團的創始成員,現在是一位中年父親,他承認自己早期作品(《青少年罪犯》)中存在厭惡女性的元素;天才的遺產透過那些在他生命中至關重要的女性的眼睛被重新評估(“與約翰·費伊一起生活,又名充滿鮮花的房間”);一位詩人表演了他寫給貓·鮑爾的信,他說貓·鮑爾的工作和公眾的痛苦可能挽救了他的生命(“致陳·馬歇爾”)。
霍珀在芝加哥的家中接受《Vulture》採訪時討論了本季的統一理念、她作為音樂作家的工作在過去幾十年裡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她如何參與該節目以及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您如何描述連結本季故事的線索?
哦,那很難。我認為這一季解決了我們最近在文化中討論的一些關於遺產的更大問題。它涉及到我們談論過去的一些方式——尤其是在音樂領域,也包括其他領域——以及我們在 2019 年將過去保留在陽光下的方式。
事情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我們製作的許多作品都試圖以一種好的方式使我們所知道的一些敘述複雜化。有時它們很複雜,因為我們是第一次直接聽到這些人的聲音,有時是因為人們受到生活中不同時刻和時間的影響,而這些時刻和時間通常基於他們可以獲得的機會以及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也許這就是那裡的縮圖。
如今,作為作家和製作人,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關於探索音樂史的一些輪廓。我們所處的數位時代,我們的歷史感,尤其是音樂的歷史感,感覺真的很扁平,因為,「好吧,如果某些東西不在 Spotify 上,它甚至存在嗎?它曾經存在過嗎?
在您看來,自從您早期開始寫作以來,音樂新聞工作發生了哪些變化?
那麼就讓我以迂迴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如你所知,過去八年新聞業發生了很多整合。如果算上雜誌的話,我猜大概有 20 個。這意味著,除非有新聞報道,或者“這個人有問題,故事結束了”,否則深入研究音樂史的機會就會減少。
但仍有許多人——音樂迷、音樂迷、音樂界被邊緣化的人——仍然想要這類故事。而且還有很多人真的很渴望告訴他們。他們有些是印刷記者,有些可能在其他媒體工作。今天很難找到更多這樣的東西了。目前在音樂新聞領域,人們並沒有被指派這些故事。
和遺失的筆記,我們覺得我們有能力和雄心壯志來講述這些故事。我們有很多人為本賽季提交了提案,以至於 [KCRW 高級編輯] Nick White 說,“我們需要四個賽季才能完成其中的一些工作。”他們真的很渴望講述這些故事,即使沒有新聞掛鉤或有太多灰色地帶之類的。
我的一個好朋友哈尼夫·阿卜杜拉吉布(Hanif Abdurraqib)——詩人、作家,也在這個季節——最近說了一些話,我轉述一下:「音樂中未經審視的過去不值得懷舊。作為一名製片人、作家和評論家,這已經成為我持久的興趣之一,而 15 年前可能還沒有那麼多。我對歷史以及懷舊所掩蓋的東西越來越感興趣。我真的很想回到這些時間和空間,然後問,“好吧,這就是我的經歷;”其他人也是這麼想的嗎?但同時「我們錯過了什麼?誰沒有在這段歷史中?此刻誰處於邊緣?
也許這只是年齡增長的功能,但也許這也是看到更廣泛的文化趕上我寫作和思考的一些方式的功能,例如,情緒 15 年前。或者,你知道,R·凱利。那時,有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掃興的人。 「嘿,夥計們,讓我告訴你們,情緒搖滾真的讓我感到疏遠,它是超級性別歧視,而且這些傢伙中有很多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然後看到它的長尾效應,讓這個立場在 16 年後得到整個文化的驗證…
不管怎樣,即使有了這個,我還是有興趣知道:我錯過了什麼?誰被從歷史中抹去了?
今天的音樂新聞格局足以解決這些問題嗎?
我認為如今千禧世代對音樂和音樂史的敏感度是憤世嫉俗的。由於某些藝術家的遺產和職業生涯是如何受到系統性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厭女症的影響而對其中一些事情產生懷疑。冒著聽起來學術的風險,我們需要質疑正典。重新審視誰重要,為什麼以及誰因為困難或因為當時的評論家和觀眾不理解他們或他們的音樂的含義而被遺忘。
您是如何成為這一季的執行製片人的?
因此,該劇的創作和製作人尼克·懷特(Nick White)和邁克·道奇·韋斯科普夫(Myke Dodge Weiskopf)找到了我,誰混合了劇集。他們伸出手來,問道:“你有興趣做出貢獻嗎?”我們開始交談,我開始告訴他們,“哦,你應該和某某談談,那麼這位作家呢,你應該和某某談談。”我有一個不會關閉的編輯功能。
然後很快就從“你有什麼想法嗎?”變成了“你有什麼想法嗎?”到“事實上,我們想和你談談主持和製作以及將你能承擔的一切都帶到這個賽季中。”
我認為尼克向我伸出援手的原因之一是幾個月前我在推特上發了一條帖子,我在帖子中問道:「由女性主持和製作的音樂播客在哪裡?它在哪裡只是女人的聲音,而不是兩個男人談論獨立搖滾或宣傳他們的新唱片的客人?這得到了大量的回應,從回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們對此有明顯的渴望——渴望了解音樂中關於女性、酷兒和邊緣人群的更深入的故事。
您還有其他正在進行中的項目嗎?
我還有另外兩個正在開發中的 Pod。我們即將推出的一款將由我和亞歷克斯·帕帕德馬斯,這將是一個連續報導的播客,它涉及真實犯罪、美國電子音樂的黎明、毒品和 80 年代的縱欲高峰。那會非常有趣。
另一篇是關於 riot grrrl 的。 [Bratmobile 的] Allison Wolfe 對這場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有一個關於 riot grrrl 歷史的播客,我們即將推出它。
我還在開發其他一些紀錄片項目,但明年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寫我自己的關於 1975 年流行音樂中的女性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