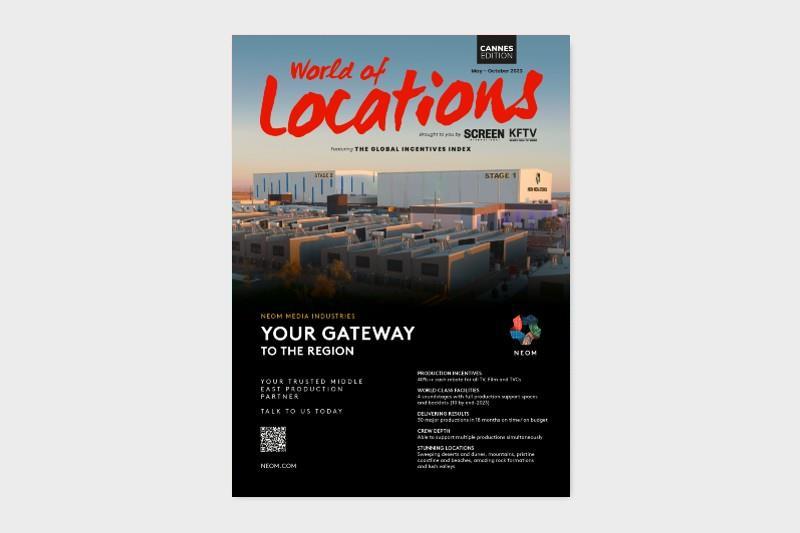由於 Covid-19 病例數量激增,問題更加複雜化,巴西製片人正在努力尋找方法,讓因資金凍結而陷入癱瘓的國家視聽產業重新站穩腳跟。
國家電影機構 Ancine 於 2019 年 1 月停止資助後,Covid-19 大流行席捲全國,並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巴西電影業陷入更深的混亂,持續的健康危機正在嚇跑國際合作夥伴。
「在疫情爆發之前,很容易找到對我們正在開發的項目感興趣的國際合拍公司,」丹妮拉·托馬斯(Daniela Thomas) 電影的製片人貝托·阿馬拉爾(Beto Amaral) 說道,該片入選2017 年柏林影展落潮是與葡萄牙聯合製作的。
「現在我們處於擱置狀態,」阿馬拉爾補充道,他正在尋找歐洲公司共同製作托馬斯的下一部電影,馬努,預算為 900,000 美元。到目前為止,製片人只獲得了 45,000 美元的資金來講述透過青少年的視角看到的巴西政治體系的腐敗故事。
據視聽部門估計,巴西有 400 至 600 部電影和電視項目陷入停滯,等待資金發放。過去 12 個月幾乎沒有拍攝任何影片,除了蘇珊娜·加西亞 (Susana Garcia) 的我的媽媽是海賊王3(我的媽媽是角色3)。
該電影是一部成功系列電影的第三部,總票房收入 6800 萬美元(3.5 億巴西雷亞爾),由 Midgal Filmes、環球影業、派拉蒙影業和 Globo Filmes 聯合製作。
「就作者電影而言,如果沒有任何新的激勵政策,它們就處於死亡邊緣,」費爾南多·梅雷萊斯(Fernando Meirelles) 的O2 Filmes 合夥人安德里亞·巴拉塔·裡貝羅(Andrea Barata Ribeiro) 指出。 「2018 年計劃開展專案的生產商尚未收到任何進展。
多個項目受到影響,例如驚悚片西卡《O2》是費爾南多·梅雷萊斯 (Fernando Meirelles) 之子奎科·梅雷萊斯 (Quico Meirelles) 的首部影片,O2 通過為不同平台製作劇集和廣告活動而生存。
「小生產商的崩潰已經發生。二十年來對視聽產業的激勵措施正被拋棄。人們明顯渴望瓦解文化。現任政府反對自由文化,」裡貝羅說,他指的是雅伊爾·博索納羅的極右派政府。
安辛沒有回應螢幕要求發表評論,但該機構將其營運崩潰歸因於會計錯誤,這將使 Ancine 無法履行正在考慮的項目。儘管已承諾投資總額為 1.85 億美元(9.44 億雷亞爾),但視聽部門基金(FSA)的財務資源僅為 1.44 億美元(7.38 億雷亞爾)。
從海外吸引資金可以拯救當地生產商。以聖保羅市為例,其想法是為需要與巴西公司相關的國際製作提供現金回扣政策。
截至今年年底,該計劃將開放註冊,旨在吸引當地最低支出為 392,000 美元(200 萬雷亞爾)的項目。製片人將獲得全部或部分在聖保羅拍攝的長片、動畫、連續劇和廣告活動總費用的 20%-30% 之間的補償。
去年,該市舉辦了來自其他州和其他國家的 1,077 部作品,創造了超過 25,000 個就業崗位,並公佈了 1.1 億美元(5.61 億巴西雷亞爾)的預算。
隨著巴西各地Covid-19感染率飆升,問題是,在博索納羅政府對健康危機的管理不善損害了該國聲譽後,聖保羅能否指望國際生產商前往巴西旅遊。
「毫無疑問,巴西目前的局勢造成了國際影響,」電影製片人、Spcine 總裁 Lais Bodanzky 說道,該公司成立於 2013 年,旨在為該市製定和實施公共視聽政策。 “因此,我們澄清,聖保羅市有具體的現實情況,與聯邦政府的言論不符。”
儘管有博索納羅的政府指導方針,巴西每個州在衛生協議方面都擁有自主權,包括強制隔離的決定。
目前,聖保羅市正在準備進入重新開放計畫的所謂「綠色階段」。黃轉綠的標準之一是病床佔用率必須降至60%以下
在該市重新開放餐廳、酒吧、健身中心和美髮沙龍後,電影院也將隨之開放。影展定於 8 月 13 日重新開放,但影片尚未選定或公佈。
「我們的想法是用當地獨立發行商的小電影來試水,」負責編制這些數據的當地影院跟踪公司 Filme B 的總監 Paulo Sergio Almeida 說。
大約 40 部巴西電影已經準備好,可以成為新節目的一部分。其中包括 Julia Rezende 的那我就是那個瘋狂的人(失去我的彈珠,如圖),Rene Sampaio 的愛德華多和莫妮卡, 哈爾德‧戈麥斯瘟疫山羊, 馬科斯·普拉多令人毛骨悚然和佩德羅·佩雷格里諾的懷疑。
但阿爾梅達並不知道這些電影是否適合業界面臨的危機。 “它必須是具有真正市場力量的東西,”他說,“因為觀眾不會冒著生命危險或花錢,除非他們確信自己絕對不會錯過電影院裡的那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