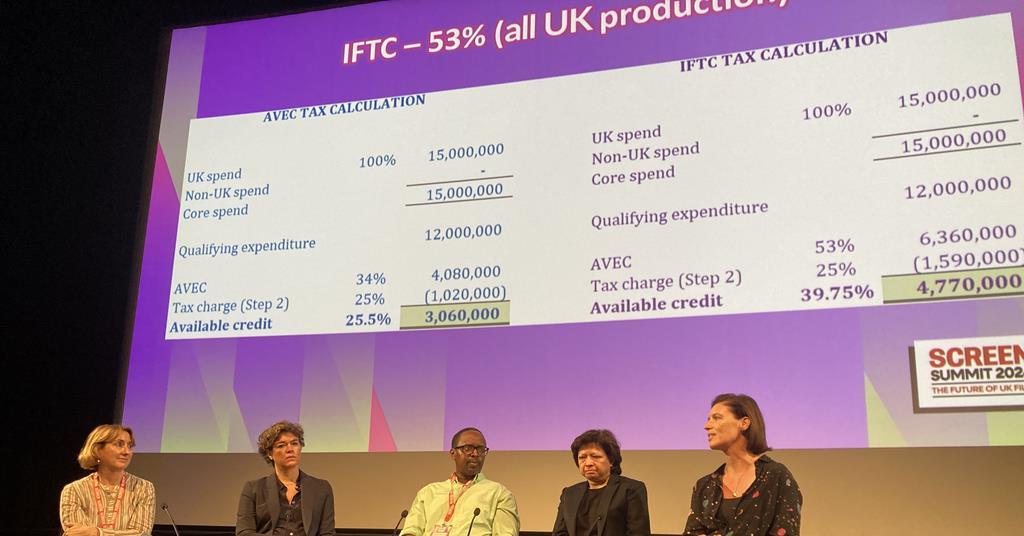你知道比閱讀一天更糟糕的是 鳴叫?為什麼,您可以通過閱讀非常非常長的Marjorie Taylor Greene推文開始一天,其中GOP代表曲折地提出了實際觀點,幾乎達到了終點線,然後完全失敗了任何。
在一個仍然保留了以前的理智的世界中,整個政治景觀不是一個迎合瘋狂暴君的異想天開的聲音的馬戲團,在這種情況下,正直和尊重是候選人不得不表現出來才能崛起的最低要求為了權力,像Marj這樣的人將被視為公共敵人。 1,如果除了事實之外什麼都沒有有幾個任期。諸如妨礙司法,濫用權力,偏愛,粉飾的術語,那將是對於我們破碎的後現代主義世界中我們破碎的民主的MTG。
如今,瑪傑(Marj)花了很多時間在X上,以至於感覺就像是想著她,也會召喚一條關於民主黨如何摧毀我們國家的漫長的推文。當她不這樣做時,MTG喜歡向她的Maga夥伴犯罪的同伴拋棄陰影,這使人們相信整個聚會是遙不可及的一天,而不是完全崩潰。
代表的最新推文是一條漫長而漫長的努力,試圖告訴她的選民,眾議院尚未提出一項計劃,以給特朗普給他的“大賬單”,瑪麗巧妙地詢問了發言人邁克·約翰遜,並敦促她的黨派派對,並敦促她的黨派派對,並敦促她的黨派給她的政黨,並敦促她的黨派給她的黨派。 “只是開始做某事。”
Marj肯定會花時間到達重點。有一次,她甚至詳細介紹了共和黨留在冬季度假勝地的地方,這顯然是“一個了不起的度假勝地,天氣晴朗,在70年代。”
作為一個用戶措辭我們都在想什麼,有懸崖音符版本嗎?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可能已經刪除了X上的限制,但這並不意味著Marj應該像她自己的個人日記一樣對待平台。
有懸崖筆記版本嗎?
-Artie Vandelay(@Artievandelay1)2025年1月29日
另外,回到原來的觀點,MTG是否以某種方式暗示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並沒有做他的工作,儘管特朗普竭盡全力捍衛他作為演講者並將他的支持拋在那個人身後?
MTG…您是在說不說……。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沒有做他的工作?因為如果他只是吸收勝過陽光,那麼也許在所有人上任之後,我們應該尋找新的演講者?
- 格拉迪斯·克拉維茲(Gladys Kravitz)。 (@gladysk06040782)2025年1月29日
其他共和黨人仍然沒有對約翰遜的不足之處進行,而且由於馬喬裡(Marjorie)給他們成為眾議院議長的完美開幕,他們並沒有錯過他們的投籃。
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在第118位使我們失敗了,他會在第119位失敗嗎?
- Gunther Eagleman™(@gunthereagleman)2025年1月29日
不過,我必須給Marjorie一件事,因為這可能是她過去六個月中唯一說的真相。這位女議員在她雜亂無章的冗餘推文之間的某個地方完美地封裝了特朗普政府一周後的局勢,我們不同意:“我們的國家已經在沉沒。”
Marj結束了她的推文,說她希望擬議的計劃不是“一張賬單上有成千上萬的頁面拋棄了我們的閱讀少於72小時”,然後補充說:“但是為什麼我期望有什麼不同呢?”伙計們……Marjorie…Marjorie終於獲得了自我意識嗎?地獄會在她繼續進行任何形式的救贖弧線之前凍結,但是我們肯定在政治領域見證了陌生人事物。